 陇首云(陇首云) 陇首云(陇首云)
|
|
|
1 楼:
[法]亚历克西·勒卡耶:马克思夜访福...
|
03年11月27日01点05分 |
马克思夜访福尔摩斯
[法]亚历克西·勒卡耶著 邵济源译
伦敦,一八七一年四月。一天,年轻的福尔摩斯在他的寓所接待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名叫卡尔·马克思的革命家,他正遭到法国梯也尔政府和德国俾斯麦首相雇佣的杀手的追杀。福尔摩斯同意帮助侦察这名杀手,但他自己也几乎陷入这桩谋杀事件之中。追杀最初是在伦敦,后来事件发展到巴黎,福尔摩斯也潜入巴黎,当时巴黎公社的起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以上是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勒卡耶(Alexis· LECAYE)所著小说《马克思夜访福尔摩斯》的开始情节。其中有些地方涉及到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公社起义期间的活动,以及一些与此有关的人物和背景,都是历史事实。该作者还发表过小说《腐化》(La Dissalulion)和科幻著作《天堂的强盗》(Les pirates du Paradis),深受法国公众的喜爱。本书一开始就描写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的不同寻常的见面:一个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个是探案小说中家喻户晓的私家侦探。他们戏剧性的见面,睿智的思想交流,最后互相了解并一致合作以对付政治阴谋的过程,读之颇为引人入胜。本刊将连载这部小说,以飨读者。
第 一 回
这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提笔了,至少对于编写我的回忆录的一个章节来说是如此。其它的事,我都心灰意冷了。那么,这突如其来的写作冲动,这难以抑制的描绘已经逝去的黯淡轮廓的欲望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只有一个解释:我老了。假如不是上了年纪(其实我一直腿脚灵活,而且右拳有非常强的击打能力),我会从容地回顾过去,不是为怀旧,而是出于好奇,出于欲望或出于遇事早做准备。
我这里要追忆的事情(追忆一词并不太确切:除了几个如今已完全消失了的人物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和它的结局),以及其它一些事情,对我的青年时期影响很大。这一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我个人的范围。在那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该事件可能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甚至以后的年代还会受到影响。
如何影响?在哪方面?我现在还说不清,为时尚早。
年过五十,我拥有一个男人想要的一切:一个牢靠而忠诚的朋友,一些智识界人士对我的尊敬和好评,虽然这样的人不是很多。至于我的敌人──可以说多如牛毛──我可以毫不吹嘘地说,不管是在伦敦、在全英格兰、还是在整个欧洲大陆,我都能让数百个流氓无赖头脑清醒,胆战心惊。为使我的自画像更完整,我们来看看我的明显缺点:我脾气有点暴躁,但我的两个毛病犯起来的时候都不伤害人,甚至还特别有趣:一是引起我朋友的血压升高(他担心我的健康,其实没有必要),另一个是我对音乐的不可救药的狂热,能把我周围的邻居们气晕过去。
我的既非常明显,有时又十分不易察觉的优点及这些毛病(加上其它毛病),部分是来自我的遗传基因,部分(我以为是主要部分)是以后的遭遇决定性地磨炼了我二十岁的软弱性格,使我潜在的天赋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扫我的优柔寡断,模梭两可以及容忍之道培养的诸多缺陷。
伟大的达尔文明确指出,在某些有利的环境中,一个物种的特性和变异倾向于保留下来,而在另一种环境中,其特性和变异就可能毁灭和消失。
在自然界中,几百万年才能实现的东西,对于人来说,我坚信只要几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人在其灵魂和肉体通过青春期的最后几道关口的忧郁时期,对于他成熟年龄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
因此,一些事件,一些冒险,一些巧合,一些机遇,常常能引发深藏在人体内的潜在能力,使其智慧达到某些领域的最高峰──要么相反,磨平或消灭其作为人的独创性和想像力,将其埋葬在平庸和无所作为之中。
至于我,我亏得这个奇遇中的幸运之神和困难环境,使我得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一个在许多方面并不完美,但在另一些领域却有着非凡成就的人物。
但,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我的整个上午都不得不为我那第一封信忙碌着,这封信是整个事情的开端。我的女房东的难以置信的愚蠢以及她的人人称道的好心肠,导致我可笑地耽误了很多时间。这位善良而又勤快的太太永远也不会理解艺术家似的随便和不拘小节的观念和习惯,我称这种观念和习惯为乱而有序。但对于她来说,这种高深的观念和习惯,除了意味着杂乱无章和到处灰尘而外,毫无可取之处。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只喜欢──她脑子里也只有──秩序。
对于一个好学而又好奇的喜欢探索的人来说,在他对一些表面看来并没有多少关系,但事实上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在联系的事物进行研究的时候,有什么能比秩序更致命和更具有破坏性呢?她的木头疙瘩脑袋如何能够懂得,如果一件事物酷似另一件事物(平庸智慧看不见),绝非由于偶然的巧合,而是像天体之间万有引力那样,由于彼此之间有着绝对必然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不管我的朋友和临时搭当怎样说,怎样写,我确切地知道,地球始终在围绕着太阳转。)
这封信,我记得很清楚,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的,旁边还有三支短小的毒箭,以及一个带有滑动盖子的象牙匣子,一件单独寄的纪念品。那么,这三样东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悬念。人们一般认为我遇事从不十分激动,人们是对的,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要保存这些证据,虽然不是活的,至少也是实物。然而,我内心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几乎使我神经失去平衡,陷入极度的烦躁、慌乱和恐惧之中,这种现象在我身上很少有过。
按照我的房东赫德森太太的原则,为了维持一个和谐的世界,应该把欧洲大陆凹凸不平的边沿削平,用直线划定边界,按棋盘一样的方格划分土地和国家,小的和小的在一起,大的和大的在一起,棕色人种,红头发人种都各有自己的位置,最后,不要忽略了那些由于不同颜色的眼睛和无药可救的肥胖以及其它因素造成的次等阶层。
仅仅是由于我对所贴出标签的精神的了解,我最终得以在帽盒子的底部找到了那封信,盒子里至少装有一千三百四十四封信。这似乎就像是在一个干草堆里找一根针那样难。我从未试过。但赫德森太太信得过我的天才,认为我能找到:她要我找的不是一根不易觉察的针,而是一张特殊的纸。
信的纸质很一般,有点发黄。右上角上有英国博物馆的标记。这不是一张公文用纸,长期读者只要花上几个便士就能买到一令。字体很小,尽管字与字之间距离很大,还是有点难于辨认。书写的直笔划一会儿歪向左边,一会儿歪向右边。这几行字给人的总印象是写信人正当盛年,但身体不太好,仅管有些莫名的犹豫,但始终为一个不可动摇的意志而激动。此人可能非常聪明,但性情急躁(信越往下看,文字越来越不清楚)。
我对公开这封信还是犹豫不决,虽然它的内容无足轻重。是否让这整个故事湮灭呢?今天,此事的圆满结局也许使而今在世的一个或两个当事人对我表示感谢。但明天又如何呢?人们将会怎么想?无情演变的历史,照样还会随潮流发展下去。我唯一坚信的是我始终没有违背我的良心。下面就是那封信。
当我第一次浏览时,觉得十分平淡无奇,一点也想不到会发生后来的事情。
亲爱的先生:
一位我们共同的熟人向我详细谈到过你。虽然你很年轻,但没有任何复杂的奥秘是你不能搞清的。朋友一再向我肯定这一点。
十三日晚上,能否给我一点时间,以便向你谈谈令我十分担心的事情(至要)。
向你致意
卡尔·马克思
我承认,这个名字并未在我脑子里引起任何回响。同样的信,如果署名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冯·凯库勒,或阿奇博尔德·斯科特·库珀,我这个年轻化学家的心脏无疑会停止跳动。我对化学的投入程度,要远远超过政治。马克思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欧洲大陆的德意志和犹太血统。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伦敦,这个古老世界的民主政治独一无二的首府,曾经是(现在更是)闲散流浪之徒、四海为家的避难者、阴谋家、各种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崒会之地,再加上这些人士的后面,至少还要跟着一个他们要推翻的政府派来的密探。英国人有口皆碑的宽容,面对欧洲大欧这股仇恨的浪潮和骚乱,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不可避免地生出一些反感和愤怒。加上普法战争,使得平常由两三个人行动的组织的数量以及他们行为的疯狂程度成倍增加。
但,当你处在二十出头年龄的时候,而你又选择了要成为正义支柱和匪徒们最大对手的时候,你是不会对摆在你面前的第一桩案子的困难吓退的。
四月十三日晚上,我草草地收拾了一下我离大英博物馆几步远的蒙塔古街小小寓所的房间,把小药瓶、蒸馏罐、长沙发下面的毒气制品、尖嘴壶、试管以及其它沙发靠垫下面和壁炉上堆放的书籍后面的其它仪器通通掩藏起来。最后一分钟,我想起来要给那间充满着并非完全无害的蒸气的小屋通通空气。
虽然在这些事安排妥贴之后,外表上已看不出什么破绽,我过一会要伪装我的身份,这时我随便看了一下天气:天高云淡,这在四月的伦敦是少有的,刺骨的寒风使稀少的行人缩着脖子。这股寒风也吹进了那间小屋,正好吹走了残留的烟味,但同时也不客气地把忘在一堆书上面装满盐酸溶夜的试管刮倒。
门铃响声吓得我差点爬在地上。这时我正在用水冲刷地毯正在冒烟的大窟窿,这条毫无用处的旧波斯地毯已被两代人的靴子踩过。换衣服已来不及了(尽管裤管膝盖处有些泛黄),去开门之前,我仅仅有时间把装水的桶放在书桌下面。
门口站着一个年约五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个头中等偏下,穿一套略旧的深色礼服,袖子有点肥,估计穿衣者不是向一位比他胖的朋友借的,就是他骤然消瘦了。他脸色发黄,微带病容,加上他双目下的紫黑色眼圈,使我倾向于第二种假设。雪白的衣领,打腊的高帮皮鞋,他穿戴的其余部分是无可挑剔的。一脸过早变白的大胡子,这样的胡子在欧洲大陆的某些阶层里是很时髦的,胡子使劲向上卷曲,超过了他又浓又黑的上唇髭,遮住他脸面的下部,但没有盖住他那带有嘲弄皱褶的宽阔的嘴巴。然而,这些细节一点都不重要,它们使我第一个印象产生错觉。在他的表情和眼神的非凡的勃勃生气面前,所有的细节,包括苍白的面孔和黑眼圈,在我眼前都一闪而过,迅即消逝了。他浓黑眉毛上方,宽大而凹凸不平的前额很高,上部稍微有点秃。额后的大脑袋里,一定藏着异常惊人的智慧。不管此人来向我说什么,我都会听他说,肯定不会浪费我的时间。
根据穿着,他不会很有钱,境况可能摇摆于贫穷和富裕之间:他的皮鞋虽然质地极高,但换过鞋底。从他的外表上看得出,他身上有着既细致讲究,又粗犷随便的奇异混合特点,这一点在他写的字里,已使我惊奇不已。
他轻轻扶在位于门铃绳子一端的壁炉架上的右手,短小、多毛而结实有力,指节末端和指甲周围呈青兰色。他随着我目光所示的方向,脸上露出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
──墨水,大英博物馆的墨水。它如同你在英国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质量非常好。根本擦不掉。我能进来吗?
我立即侧身让开,意识到自己老盯着人看可能有点不礼貌,但来人并未显出生气的样子。
这时,我已听出来了,他是德国人。他发音非常标准。重音带有一种有穿透力的金属声。他一边进屋,一边在转身面对我之前,迅捷地把我简陋的住所扫了一眼。
──是化学家?
我以沉默表示承认,我非常吃惊,更多是由于他对此关注的声调,而不是由于他推断之神速。从他站立的住置,能完全看清楚沙发底下放的东西是一般家庭用的瓶瓶罐罐呢,还是专门用途的仪器。
马克思先生在继续说话之前,用手指了指一叠上面写满他那蝇头小字的、插在外衣口袋里的文稿:
──我很高兴同一个搞科学的人打交道。我本人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搞研究的人,毫无疑问,我们相同的身份使我们可以免去一些繁文缛节,容易相互更好地了解。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布鲁姆莱克先生非常热情向我谈起你。好像你在一桩古代手稿遗失案中干得很不错。
轮到我问他了,但问得简直有点愚蠢(在他那双手上,没有任何痕迹能证明他接触过有毒和积腐蚀性的制品):
──你也是化学家吗?
回答我时,他带着微笑。
──并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意义,尽管我非常热爱化学。我研究的专门领域是社会化学,进化中的人类社会,同样用这种方法,达尔文研究的是物种的进化。人类的社会这个对象也是非常复杂的,其变化远远超过冶金的最高纯度的提炼。
这样看来,我先前并没有猜错!又是一个相信凭自己独有的思想力量就能够改变世界的革命家!又是一个认为靠几颗炸弹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从根本上消灭专制政治的鼓吹者!我忽有一种担心的战栗:无论如何,他来此莫不是求我帮他制造某种爆破装置,拿去在马路上炸死一个沙皇或某位警察局长,或许还会陪上几个路过那里的无辜者。
马克思也许从我面部的表情上猜到了我想的什么,因为他以一种诚挚的惊奇看着我,并且暴发出一阵笑声。
我承认,对于马克思的某些同代人对他的评价,我滋生出一种强烈的反感。我从书上看到过,甚至听到过,说马克思是一个“冷酷而狂妄自大的人”,说他惯于以一种“专横和统治者”的语气同人谈话,他不容别人同他争辩,以及其它的愚蠢作风。我敢肯定,这都是那些低能蠢人对他的反应,而我的感觉完全不同──至少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这样。
他的微笑立即使我有点明白,我脸红了,我为刚才的疑心感到羞愧,而这时他还什么都没有说,逻辑上讲,他说出来就能消除我的疑虑。
──你不必害怕!我不是来向你要炸弹制造配方的。愚蠢的恐怖主义现在解决不了、将来也永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既不是一个海因岑,也不是一个魏特林。我来找你完全是另一件事情。我能坐下吗?
我把他领向长沙发,他一下子就坐了下去。当他背靠着沙发时,我分明听见一种玻璃杯破碎产生的特别声响,我绝望地试图回忆,藏在靠垫下面的试管是不是空的。
很明显,马克思一点也没有发现。眼看靠垫下并没有任何可疑的液体流出来,我认为没必要惊动他了。
他坐着时,显得更加苍老,更加疲惫。他的胸部急速地向上挺了两三次,像是要强忍住一声剧烈的咳嗽。他抬起眼睛,向着我微笑,我再次被他目光中的睿智所折服。这样的一个人,毫无疑问不会想到安放几颗炸弹去改变世界。我拖过一张凳子,坐在他面前,准备洗耳恭听。
他继续审视我,皱起眉头,以一种老师耐心开导懒惰学生的口气对我说:
──你听说过“国际劳工联盟”吗?
我一时语塞,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名称我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但真倒霉,我哪怕能说出几个字来也好!
马克思并未生气,像一位老师那样,更和蔼可亲地笑了。
──你们这些英国人,真不可思议!你们给一个让所有资产阶级和整个欧洲发抖的组织的头头提供避难所,却不想一下是对还是错,你们甚至连这个组织的存在都不知道!我如果把这同样的问题向巴黎、柏林或日内瓦的随便哪个笨蛋提出,他们都会吓得脸色发青。你,一个年轻、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资产阶级分子,你不但不害怕──我对此感到高兴──你连我们的存在都不知道!然而,你知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行动,大不列颠才没有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介入南军一方。
我不认为应该原谅我的无知。首先马克思似乎丝毫也没有感到不快,相反还有点觉得开心。其次,我事实上也看不出我们为什么必须两眼死盯着那个新想像出来的、毫无价值的杰作拉芒什海峡。何况,马克思也没容我有时间回答。
──在详述我造访的目的之前,请允许我简单说几句能阐明下文的话:战败的法国的那些失败主义叛徒们,聚集在凡尔赛阴谋集团之内,他们不仅一点也不欣赏你们对待我们的冷漠,更有甚者,他们把起义和巴黎公社的责任推在国际联盟身上──我是这个联盟总委员会的书记之一,负责德国和俄罗斯支部。事实上,在公社的社员中,特别是在那些最勇敢、最清醒、最活跃的社员中,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根据我们对法国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分析,德国总参谋部和梯也尔这群败类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暧昧不清的赌博,一切迹象显示,巴黎公社坚持不了多久。根据梯也尔和法夫尔的穷凶极恶,公社很可能会接受一个异常悲惨的结局。对此,那些既不愿向普鲁士人投降,也不愿俯首听命于叛徒的真正法国人十分清楚。他们所有的人都准备死在特罗许的机关枪子弹之下或新克里多尼亚和中美洲的苦役犯监狱中。而普鲁士人得寸进尺,他们还想除掉搅得他们心神不宁的祸根。这个祸根就在英国,他们想在这儿把祸根除掉。
马克思声调高昂,双颊发红,显得非常激动。从他面部轮廓的紧张以及他嘴唇痛苦的皱褶中,我突然懂得了他对自己祖国的帝制政府和俯首听命于敌人的法国政府有多么憎恨。但,比起对于他的敌人的仇恨而言,我发现另一个更为使他愤怒的因素,那就是他确信自己对于那些他称为朋友的人的爱莫能助。我提出我想到的唯一一个问题:
──你说的“把使他们心神不宁的祸根除掉”是什么意思?
紧张从马克思的脸上消失了,他甚至笑了,有点忧郁:
──除我说过的而外,没有更多的意思,也没有更少的意思。他们想消灭“国际劳工联盟”的领导。为此,他们必然要采取断然措施。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我的伙伴中的任何一个,尤其是法国人。但这不是──起码暂时不是──他们目的。我目前是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没有我,联盟有解体的危险,如果他们想影响群众和稳住资产阶级的话,他们首先要杀死的是我。
受到他冷静而客观谈话的感染,我提出下面的问题:
──你怎么会这样肯定呢?
──啊!这并不难。即使最没有警惕性的人,他只要看到凡尔赛报刊上杀人的号召就够了。但更为严重的是,斯蒂伯和其他一些无耻之徒的叫嚣,在目前只会使人得出凡尔赛无能的结论。非常自相矛盾的是,我今天还能活着,还多亏梯也尔先生──或者说是对我的死刑命令缓期执行。他尽管非常卑鄙无耻,还是很清楚,目前还不是把英国人的愤怒炸弹引到自己怀里的时候,梯也尔的目的是促使德国人来杀我。俾斯麦首相完全猜到了这一招──小偷有的也会被偷──他不惜一切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至少暂时是这样。
──那么,现在你怕什么呢?
马克思笑了,总是那样忧郁。
──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非常之巧妙,即无耻地使法国和德国和解。他们收买了一个违反放逐令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怪物,破落贵族,反犹太分子,以及像所有俄国人一样的仇外狂徒。他们同此人在一桩卑鄙交易中达成妥协,他什么都肯干。这是俾斯麦打算同他的主子霍亨索伦大公玩的一场恶作剧,这位大公遵奉良好的家庭传统,时时刻刻准备匍匐在沙皇的脚下。
我一时无话可说,对资料来源及其细节之准备印象很深。我不能保持沉默,尽管我对这方面的事兴趣不大,还是试着想像杀手的外貌以及当他不可避免要走向他的目标的时候,他的举止是鬼鬼祟祟的呢,还是真正地表现得沉着冷静,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叫什么名字?
──茹贝尔斯基,但这个名字对你毫无用处。当他露面时,肯定装扮成另一个人的样子,使用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我的情报来自俾斯麦的一名得力助手,此人从前属于一个秘密社团,我是该社团的头头。他知道,我手头现在还掌握着他从德国寄给我的、关于德国的情报。他完全听命于我。正是此人,不久前给我送来一份俾斯麦决定趁我去汉诺威拜访我的朋友库格曼博士的机会逮捕我的通知。
──但这个叛卖俾斯麦的人,完全可能出卖你啊!
──不,我认为他不会。他太冒险了。
──杀手什么时候来伦敦?
──他已经在这里了。
我禁不住跳了起来,想像一个理论上的杀手是一回事,说杀手离你近在咫尺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交谈者大概误解了我的表情,因为他迅速地站了起来,亲切地用胳膊挽住我,把我引到窗户跟前。他轻轻撩开窗帘,用头示意让我看大街上。
──最好先看看。
我的视觉一片漆黑,但几秒钟后我就看清了,在我住所对面大楼的凹处,一个瘦长的影子贴墙站着。这时,监视者似乎凭着某种第六感觉,发现了我们在看他,他的裹得严严实实的脸,像一个白点似的向我的窗口抬起,然后很快就消失了。我们从窗口退了回来。他也可能什么都没看见。
我马上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从一个茶叶盒子里取出一支上了膛的手枪。马克思用焦虑不安的眼光看着我。他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
──毫无用处!毫无用处,我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把你的枪收好。这人只是个陪衬,杀死他或打伤他都于事无补,甚至起相反作用。我已观察过这家伙的行为和举止。他们会以另一个无名小卒来代替他。这对于一举击中我们的真正敌人毫无帮助。
我承认,我立即被他无懈可击的推理所征服。马克思重又坐下来。看我最终安静下来,一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的态度。我想可以理解为你接受了。
──请原谅,我还不十分明白。接受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对我缺乏机敏感到失望,马克思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来。
──接受保护我去对付那个要杀我的家伙。你当然清楚,正规警察在这样的攻击面前,几乎是解除武装的。更糟的是,他们还会派几个笨蛋来保护我,以英国警察特有的职业良心,他们会在别人杀我之前,就被杀死。还不用说,我的朋友们如果知道警察在保护我的话,我将成为他们的笑柄。我要有求于你的要复杂得多:那就是找出雇佣杀手,在他毫不觉察的情况下揭露他,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忍不住一声惊叫。去不动声色地杀人,这难道是劳工联盟的领袖要我去干的事吗?他抬起手,做了一个要我冷静的动作。
──不,不,你一点也不必害怕。我不使用那种方式。我所说的“消失”,意思是把他看管起来,不让他露面,或把他赶走,如果你高兴,也可以把他的注意力引开,使他不能为害。
──然后呢,我拿一个关在地窖里的俄国杀手怎么办呢?
──你看住他几个星期,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一件一直挂在我心上的事。然后你就把他放了。不要担心,他不会去起诉的。
──如果他再来杀你呢?
──我总是冒着危险的。那时他做案的紧迫性已经过去了。重要的在于,他现在不能杀我,否则将给运动带来致命打击。另外一件大事将抹掉这一切:巴黎公社的失败。至于这位茹贝尔斯基,大的困难还不在于把他置于不能为害的地位,而是阻止他将其受挫的消息通知他的同谋者,这样我才能利用必要的宝贵时间来完成这个……(马克思用手拍了拍他装着文稿的上衣口袋)。
他立即站起身来,按德国人的习惯,躬身向我行了一个礼。
──这是我的名片,明天同一时间,我在家等你。你得告诉我你是否同意。
──我陪你一道下去。
──不必了,我亲爱的先生。完全没有必要。今夜我不会有任何危险。而且,惊动他们是不明智的。
离开之前,他握住我的手,以英国方式使劲的摇了几下。我随即走到窗口,瞧着他远去,衣领高耸,脑袋缩在肩膀中间,我目送他灰色的影子大约走了五十步远,直到消失在暗夜之中。
自:《万象》杂志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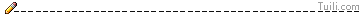
|
欢迎光临下列版块:
看《福尔摩斯》:一切以福迷为中心。(在本站“主题版区”中),品《原创推理》,评《中国侦探》:发掘历史,体验发展。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主题版区 > 福尔摩斯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主题版区 > 福尔摩斯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