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g(catsanova) xing(catsanova) 
|
|
|
6 楼:
Re:Re:[荆非]碧沚园(一至二十...
|
05年02月17日18点01分 |
十六
收工回来,走到自家门口,谢三直觉屋中有异。
推开门,屋内斜斜地亮了一片,谢三一眼便看见桌上那些杯杯碗碗。
谢三家中并无多少碗碟之物,今日却被人尽翻了出来,连藏在床下久已不用的泡菜坛子也没放过。
器皿中皆汪着水,水色泛绿,漂着片茶叶。谢三瞥眼床上那身影,心下早已明白几分,又闻屋内一股酒气,懒得多加搭理,放下手中器物便去收拾桌上杯碗。
只听“哚”的一声,一柄飞刀兀然立于杯碗之间。
床上黑影闷哼一句:“莫动。待我再睡片刻。”
谢三无奈,想沏壶茶解乏,却见那茶壶也被泡了叶子摆在桌上,只得作罢。
床上黑影翻滚两下,现出谢三意料之中那张脸。那张脸被阳光晃得白得有些刺眼,谢三不由想起很久以前在酒馆所见景象。
谢三突然心烦,猛踢床脚两下,那张脸随床板抖了两抖,遂扭向墙去,不多时竟传出鼾声。
谢三离开。
待谢三再次推开家门,荆非已趴在桌边,眼中毫无睡意,直盯着那堆杯碗出神。
谢三扔在桌上两根油条,也不言语,自转身去收拾床铺。却听身后荆非问道:“去过州衙了?”
谢三手中不停,随意道:“又非派薪之日,我去州衙做甚?”
荆非懒懒道:“这油条如此细短,明州城内也只州衙边那早点铺敢如此欺诳。且油条已尽干瘪,显见买得后又走了段路途方带回来。此地出门不远便有早点铺,这般舍近求远,你没去州衙又去了哪里?再者,昨夜我迟迟未归,回来又翻尽你家杯碗,也难怪你好奇去州衙探查。”
谢三冷冷道:“油条细短,只因旁边早点铺新换了伙计,手生而已。油条干瘪,是我懒得回来见你那宿醉丑态、有意在近旁茶摊喝了两杯耽搁所至。至于大人公干,小的向来不感兴趣。”
荆非头一歪瘫趴在桌上,连呼“头疼”。
谢三嗤笑道:“头疼呼我无用,需找陈未时陈大夫。只可惜陈大夫眼下抽不出身来。”
荆非忽精神一振,道:“陈大夫在忙何事?”
“听闻州衙赵平病重,陈大夫一直在衙内照看。昨日你与赵平同在一起,我还当你早知此事。”
荆非叹道:“我只知赵平昨夜发病,子时方略缓些被送回州衙,并不知他当下境况。”
谢三道:“你对那赵平倒颇是留意。”
荆非又捧头不语。谢三摇头,自床角摸出个酒壶,敲在荆非面前。荆非也不道谢,先灌下一口,两眼发直道:“记得你曾说过我不适合当差。”
谢三道:“不错。那又如何?”
荆非忽话题一转,道:“钱家张笈可常去州衙?”
“确实。我曾见过几次。”
“此人为人如何?”
“寻常家奴。”
“怎讲?”
“好大喜功,仗势欺人,实则鼠辈。”
荆非若有所思,又道:“这张笈嗜好喝茶?”
“不过附庸风雅。常听他吹嘘钱士清赏他好茶,那茶着实可惜了。”
“钱士清赏过他苦丁茶?”
“也许。”
荆非眼中忽是一亮,道:“若以‘吝啬’一词形容那张笈,你意下如何?”
谢三一愣,许久方道:“我与张笈交往不深,只听闻衙役抱怨:张笈时常夸耀家中多有稀罕之物,若有人要亲身去看他却又含糊起来。”
荆非静了片刻,复凄然笑道:“原来如此。”转瞬又换了叹息:“但碧沚园一事……”
谢三道:“我倒不知碧沚园又出何事,只从茶摊听闲言知晓,今日万卷楼大半藏书便要转入范钦名下。”
荆非脸色突变,酒壶凑在唇边许久方缓缓放下,喃喃道:“我不明白……”
谢三道:“售书之事,丰范两家早有商议,有何奇怪?”
荆非犹疑道:“我心中尚有几处谜团未解,但若解开此谜……惭愧,也许我真的不该当差。”
“你本就不该当差。”
“昨夜曾有人问我:我可曾纵容疑犯。”
“你如何应答?”
“我能如何应答?”
“倘若我估计不错,如非当日有人纵容,恐怕也难有今日荆非。”
荆非只笑:“你如何知道?”
“因你破案太多,擒凶太少。”
荆非长饮。
谢三道:“话已至此,你当自有分寸。”
荆非放下酒壶,道:“谢老板今日絮叨得很。既有雅兴,敢问谢老板可记得此诗:何处人事少?”
“西峰旧草堂。”
“晒书秋日晚,”
“洗药石泉香。”
“后岭有微雨,”
“北窗生晓凉。”
荆非笑道:“谢老板好记性。余下的我倒尽忘了,不妨改日再聊。”言罢抄起酒壶扬长而去。
谢三心中知道那末两句,却只抄了抹布擦净桌上水渍。又听门外远远飘回个声音:“桌上杯碗莫动,有毒!”
十七
碧沚园。
昨日晒书的内院今日堆了半院书箱。院中忙碌着范钦、去蚤并一班家丁、衙役。丰坊却不在其中。见荆非到来,范钦只上前略寒暄几句,便又忙着指点家丁清点书目装箱搬运。荆非亦不在意,找来去蚤,道:“敢问丰老先生可在?”
去蚤道:“我家老爷正在碧沚亭独坐,大人若是想见,怕要换个时日。只因老爷有命,任何人不得打扰。”
荆非会意一笑,又道:“无妨,今日不过想与你闲聊。昨日午间你为赵平送饭,确实见到他在屋内?”
去蚤眼露疑惑,点头道:“确实。小的端菜进去,正见赵大人半倚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小的进来方睁了眼,随即吩咐小的将饭菜放在桌上,说是稍候再用。”
“此后你可曾再去?”
“不曾。筵席上杂事尚顾不过来,大人也是亲眼见了。”
“我等自碧沚亭返回书房,途中见赵平正在内院。或许你凑巧知晓他是何时出的房间?”
“小的实在不知。”
此时却有一衙役施礼上前,道:“小的恰好知道。”
“仔细说来。”
“小的昨日也在这内院看守,亲眼见到赵大人在诸位大人返回约一柱香工夫前出的房间。”
“出房后他去了何处?”
“只在这内院随意翻阅些书册,并未去园中他处。小的还可为赵大人作证:诸位大人于碧沚亭筵席期间,赵大人确实在屋内歇息。”
“你何以这般肯定?”
“赵大人平日待我等弟兄不薄,昨日赵大人突发旧疾,小的心中也颇忐忑。自去蚤送菜走后约半个时辰,屋内许久没有动静,小的放心不下,推门探个究竟。只见赵大人仍睡在床上,虽是朝向墙壁,不曾看到脸面,但那身形必是赵大人无误。”
荆非略加思索,复展开笑颜道:“两位不必多心,在下不过随口一问。”
那衙役又道:“荆大人明察秋毫,想来不会疑心赵大人人品。何况赵大人如今……”
荆非敛起笑容,追问道:“今日陈大夫处可有消息?”
衙役犹疑良久方道:“听闻凶多吉少。”
荆非拂袖叹道:“在下想再多看眼赵平昔日住处,还有劳去蚤引路。”
屋内景象一如昨日,只门窗紧闭,多了几分阴郁。荆非站立门边打量屋内,确能见那床榻,证实方才衙役所言;走至床前,审视那床上铺盖,并无发现;无意间翻弄两下枕头,心中却灵光一现,急急掀起褥单,仔细察看一番,又见那床边邻墙夹缝间木板,抽将出来,在手中略掂了掂,只觉昨日似在某处见过类似物事,一时却想不起来,遂抬头问那去蚤:“碧沚园中可还有类似木板?”
去蚤咧嘴笑道:“我家老爷又不开刻坊,多要这夹板有何用处?”
荆非先是一愣,复摇头自嘲一笑,起身推开西窗,留意窗下,果见窗下杂草丛生,散落不少枯败竹枝。再看稍远之处,湖水层层漾上岸来,于岸边堆积了诸般杂物,全不似远处湖水一派清秀。
去蚤只觉荆非举止古怪,却也不便相问,见荆非夹了那木板匆匆出屋,忙也几步跟上,不料荆非忽地停步,险撞在荆非身上。荆非俯身,自地上拾起张白纸。那纸与书册一般大小,前后皆不见字,唯边缘上有两处被扯裂小孔。荆非好奇道:“这是何物?”
去蚤凑近扫上一眼,道:“不过是书中衬纸。书册老旧难免装订脱落,常有衬纸掉出。”
“书中衬纸有何用途?”
“衬纸插于折页之间,有助书页耐久保存。也有因印字纸张过薄、在折页间夹以衬纸避免字迹透光模糊的。”
荆非打量手中木板,不禁一笑,忽又想到什么,复凝视去蚤,道:“你家老爷藏书可是全部让与范钦?”
“并非全部。老爷仍自留了些普通书册。”
“昨日赵平送来那新刻地方志可曾转与范钦?”
“小的不知。”
“那地方志以锦盒装匣,且簇新耀眼,或许你曾瞥见。”
去蚤思索片刻,兴奋道:“今日小的曾在老爷书房见到。书房内所收皆是老爷自留之书。”
荆非朝那去蚤一笑,回视院中书箱,眼中却溢出苍凉之色,喃喃道:“可惜我仍不明白。”
去蚤不解,正欲试探细问,却见有衙役急急奔来,跪倒荆非脚下,叩首道:“贺知州请荆大人务必拨冗前往州衙,赵大人……”
话音未落,已不见了荆非踪影。
十八
荆非不怕见死人,只怕见临死之人。
见到床榻上赵平,不用看旁边陈未时与贺知州脸色,荆非便知自己此番来明州实在运气太差。
赵平却只笑看荆非臂下所夹木板。
荆非轻轻放下木板,向贺知州长揖一礼,道:“下官斗胆,敢请贺大人回避。”
贺知州面露惊诧,但见赵平笑而不语,只得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荆非又看陈未时。
“日昳不是外人,大人尽言无妨。”
荆非不语,只递上那木板。
赵平奋力起身接过,旋即力竭倒下,气促了半晌,方略平和些,道声“多谢。”
陈未时看眼赵平,转向荆非:“这木板乃是先生所赠。八年前师生不和,双九愤而离去,一怒之下不曾带走。”
赵平低咳一阵,嘴角沁出些粉红血沫。待陈未时帮他小心擦净,赵平挣扎道:“大人既将木板带来,想必碧沚园一案已破。”
荆非道:“赵兄与在下有约在先,在下怎敢怠慢。”
听闻此言,赵平气息倒似平和许多,虽一时说不出话来,仍以眼神示意荆非继续。
荆非一字一句道:“《春秋经传集解》真本实在赵兄手中;《尚书》失踪及张笈暴毙,同是赵兄所为。”
赵平微笑,略一阖眼。
荆非一叹:“若定要证物,以在下判断,那碧沚园旧屋西窗窗外若要细勘,仍有蛛丝马迹。可惜以今日情形……所谓证据,已无关紧要。”
赵平勉强稳了气息,道:“大人不妨从头讲来。下官落魄一生,难得听到自己的故事。”
荆非凄然一笑:“《春秋经传集解》真本失窃之事,截至毕老汉身亡之时,想来赵兄与在下有同样推断。”
赵平挣出三字:“钱士清。”
“不错。在下因入园前已经人提醒盗书之事,故多留意了些。当日初闻赵兄一味强调碧沚园内现藏《春秋经传集解》为伪,在下更警惕几分。随即赵兄病发,在下只当赵兄力不从心,便逞能接过这惩凶职责,代赵兄揪出钱士清,却不想一切本在赵兄计划之中。”
荆非看眼赵平,继续道:“赵兄将众人注意集中《春秋经传集解》之上,实为达成两便。一为点明万卷楼失火兼毕老汉身亡祸首,再为借机窃取《尚书》。那《尚书》与《春秋经传集解》同侧,以赵兄心计及平素交往,早知尧卿将购万卷楼之书,最是在意万卷楼藏书真伪。虽尧卿先前留心《尚书》,但若听闻《春秋经传集解》可能有伪,必也将心思聚在那《春秋经传集解》之上;丰老先生恃才傲物,断不会承认自家藏书有伪,故全力相争亦在情理之中。其余诸人,虽是凑个热闹,但也因此忽略其他诸书。包括在下,因赵兄暗示那《春秋经传集解》真伪涉及命案,在下亦多对此书留意一些。于此情形之下,怕是无人再有心思顾及桌案上其他书册,如此赵兄大可于我等争端起时佯作被先生斥骂,后退几步,寻无人注意之机,将《尚书》纳入怀中。然而,赵兄举动瞒不过有一人眼目。陈大夫,在下所言可符实情?”
陈未时不语。
赵平眼望陈未时,淡淡笑道:“此案不关日昳,其中种种皆是下官独自谋划。”
荆非叹道:“赵兄此计,最高明之处便在无需同谋、却人人皆是同谋。钱士清之做贼心虚,尧卿之嗜书如命,丰老先生之孤僻倨傲,贺知州之附庸风雅,陈大夫之超脱淡漠乃至在下之自以为是,皆被赵兄利用。赵兄清楚:即便陈大夫有所察觉,只会与自己私下商议,必不会当众点破。赵兄故意激怒丰老先生,令之后自己病发顺理成章。旁观我等皆以为赵兄病发乃是与先生争吵、火气攻心所至,不曾料想这病发一场亦在赵兄窃书计划之中。”
陈未时只道:“当时双九确实病发。”
荆非道:“赵兄清楚:若假作病发,瞒不过陈大夫医术。所谓久病成医,赵兄于自身状况了如指掌,明白自己只需略为入戏,便可假戏真做,确实心疾发作。心疾发作者最忌颠簸,故赵兄有十分把握陈大夫不敢涉险将自己送出园去。加以丰老先生在场,若见赵兄病发,必吩咐陈大夫将赵兄送至昔日所住旧屋歇息。赵兄深知陈大夫熟悉自己禀性,待病势和缓后不会强留屋中看护,如此旧屋只剩赵兄一人,而赵兄下一步计划便在这旧屋内实行。倘若在下推断不错,当时赵兄身上除那《尚书》还有一书。”
赵平略一阖眼。
“那书恐怕便是贺知州昨日赠与丰老先生之地方志。赵兄以地方志掩人耳目,称得上高明之举。那地方志乃赵兄监督刻印。赵兄明知丰老先生素来不喜装祯华丽之书,却刻意以锦盒匣装。贺知州附庸风雅,自不会反对将记录自身政绩之书精装留传。选择曝书之日送上此书、以及‘与前人之书同曝’之说,怕也是赵兄此前暗示过的。以贺知州性情,能见自身政绩与前人功业同列,早就求之不得。以锦盒匣装,目的之一便是有意令丰老先生不快,否则难以引出‘与前人之书同曝’之说。丰老先生虽是倨傲,却不致当面令贺知州难堪,必会吩咐赵兄,将此书归入地方志类同场曝晒。倘若丰老先生当时将地方志单独存放,赵兄后续计划难以实行。因赵兄并未真正将那地方志留在院中曝晒,而是趁无人注意偷留怀中,于院内柜板上只留下锦匣。院内书册繁多,草草望去,若见那锦匣,常人便当那匣中之书就在一旁曝晒,难以料想匣边之书实是另外一册。”
“转回赵兄独留旧屋之时。昨日午间赵兄确实不曾离开旧屋,除有去蚤作证,今日还有一衙役主动作证昨日曾见赵兄于屋中安睡。可怜这衙役一片好心,不曾料想恰是他这证词最终验证在下对赵兄之怀疑。依那衙役所言,他昨日因放心不下推门探视,见赵兄面向墙壁安睡。在下本未听出异常,重新查看旧屋床铺方觉有异。那木床东西向依墙摆放,枕头位于西端,赵兄若面墙而睡,必是左侧躺卧。如此卧姿,于常人或许无妨,但有心疾者断不会这般躺卧,只因左侧躺卧必压迫心脉。那衙役却见赵兄以此等古怪睡姿躺卧,只可证明赵兄当时确有不得已掩饰之事,而那不得已掩饰之事便与这木板有关。昨日赵兄主动告知在下床边与墙壁间藏有木板,先发制人,打消在下疑心;又道出这木板乃是垫衬之用,令在下忽视了木板原来用途。”
赵平轻抚身边木板,道:“这木板本是刻坊常见夹板。”
荆非道:“在下惭愧,于刻坊之事所知甚少。今日见这木板,只觉眼熟,待去蚤说出‘夹板’一词,在下方醒悟昨日曾于文秀书堂刻坊见到类似物事,想来必是装订书册之用。可惜今日时间紧迫,尚不及前往刻坊仔细询问,倒要烦劳赵兄指点这夹板究竟有何用途。”
“压书、锉书、上皮时夹书所用,通常为一对。”
“如此便是了。若非今日于碧沚园内偶见书内衬纸脱落,只恐在下至今难以想到赵兄将那《尚书》藏于何处。昨日尧卿曾言,宋版书册多为蝴蝶装,版心向内,只以浆糊装裱,时日稍久,书页便易脱落。那《尚书》乃丰老先生祖上所传,想来亦为蝴蝶装,至今经日已久,若要将书页拆卸,恐怕并不困难。”
赵平微笑。
“昨日午间,待旧屋无人进出,赵兄便将所藏地方志并《尚书》同拆解开来。地方志乃是新书,原本不易拆解,但此书为赵兄监督刻印,若于其中一册略做手脚、使装订松散,想来并不困难。地方志以当世流行包背装装订,与蝴蝶装比较,除增以纸捻穿订、浆糊裱背外,最大区别乃是版心向外,书页外折而非内折,文字皆显露于外。《尚书》日久纸薄,文字向内折叠,兼以长期存放书库,纸张受潮,印墨中又多含胶质,难免彼此粘连。若非细看,两页粘连颇似无字白纸。赵兄便以这拆解下《尚书》书页为衬纸,插入地方志书页之内,再将《尚书》原书封皮匿入地方志封皮并护纸之间,重新装为一册。《尚书》不过薄薄一册,夹带入地方志绰绰有余。先前所言那地方志赵兄刻意以锦盒匣装,最要害处却不在锦盒,而在盒中之书。若是普通装订书册,书册大小相去不远,惟有精装之书,常较普通书册大出一些。赵兄欲施之计,于这书册大小关系甚大。只因这地方志书页大小大过那《尚书》,寻常翻阅更难发现夹于书页中之衬纸。赵兄家中本是刻工,于书籍装订当较常人熟练。夹板虽非成对,赵兄仍可利用木板与床板同将加工后书册夹制成形。先前所言那衙役曾见赵兄面墙而睡,其实赵兄乃是听闻有人推门、一时仓促,不得已面墙而卧,挡住床上书页乃至夹板。因新裱书册浆糊未干,木板并床板靠墙一侧便带了些潮气。”
“装订书籍必备之浆糊,想来是赵兄藏于竹管类容器内偷带进园,事后由旧屋西窗丢至窗外湖中。赵兄久于旧屋居住,自然知晓那窗外本有荒竹,湖水中漂些竹枝乃寻常之事。至于拆解书页及打孔穿捻工具,在下推断亦是竹篾一类。新制之书,难免泛潮,若在常日,并不难于识破,然昨日正逢曝书之日,所有书册皆置于日光下曝晒,反混了众人眼目。赵兄将地方志重订完毕,依然收于怀中,步入内院,借翻看书册、无人留意之时重将地方志放回原处。一册《尚书》便就此消失。”
赵平一笑,道:“大人明察,只错了一处。那《尚书》珍贵,下官岂敢莽撞打孔穿捻。下官早用轻薄纸张两张裱为一张,中留空间,于地方志书页内加衬。昨日所为,不过将《尚书》书页分置衬纸夹层而已。”勉强说完,又咳喘不已,似有不支之状。
陈未时眼疾手快,于赵平要穴处刺入银针,捻动一番。半晌赵平终缓过气来,脸上却益发现出灰紫之色。
十九
赵平歇过片刻,气息微弱道:“大人何时起的疑心?”
“钱士清伏法、尧卿发现《尚书》失窃之时。”
“因何缘故?”
“若无《尚书》失窃,在下或仍沉浸自得之中。《尚书》失窃,反令在下直觉钱士清一案太过顺利,仿佛一切早有人加以安排。即便如此,当时在下只有隐约不祥之感,尚不知晓钱士清等等不过赵兄计划起始部分。初步验证在下心中疑惑的,乃是赵兄对外贼进入那番推断。赵兄当时表现可算得古怪。以时机论,丰老先生于席间返回书房、取走《尚书》最是可能;且那书原为丰老先生所有,若丰老先生因故收起此书,本就无可厚非。赵兄却不知因何缘故,定要坚持《尚书》已经被窃,又竭力澄清在场诸人嫌疑,生造出一身手高强之外来贼人。赵兄那番虚中生实之推论着实高明。在下向来自诩行事缜密,不甘忽略任何可能细节。不想昨日这点自得之处又被赵兄利用。赵兄清楚:此番推论一出,以在下禀性,既不能强令赵兄寻出外贼入内证据、同时亦找不出反驳赵兄推论之证,最终被在下自身思路束缚了手脚。可惜赵兄不曾料想,正是这番推论令在下猛醒,顿悟赵兄早将我等心理操控于掌间。依此思路重新回想钱士清诸事,虽仍有诸多疑团不甚明了,在下已然确信:那幕后身影确实存在,正是赵兄。”
“但在下仍是迷惑。正如赵兄所言:所谓偷窃,无非意在据为己有。当时在下尚不清楚赵兄究竟以何种手法藏起那《尚书》,却也猜想必与那锦盒或地方志有关。但那地方志显将存留碧沚园内,赵兄如此费尽心机,却不将书带走,此为在下心中疑团之一。再者,昨日丰老先生因钱士清一事大受刺激,陈大夫已吩咐我等切勿打扰,如将《尚书》失窃一事归于丰老先生所为,相信当时亦无人敢于前去查证,如此岂非于赵兄更为有利?但赵兄却定要令众人确信那《尚书》已被窃,实在与寻常窃书人心理不符,此为疑团之二。”
赵平淡淡一笑,道:“如今大人于在下手法已了如指掌,却仍不明白在下动机何在?”
荆非摇头:“惭愧,在下至今不明。当日于碧沚园中,在下隐约觉察赵兄歇息旧屋内当有蹊跷,若搜得蛛丝马迹或可解开在下心中疑惑。可惜,在下就此犯下大错。”
“大人悔恨当时纵容了下官?”
荆非惨笑道:“在下如今只想确认:‘纵容’一步并非赵兄计划之内。倘若在下有如此之多弱点可资利用,在下真该回家种田去了。”
赵平看眼陈未时,道:“大人过虑。《尚书》一事,下官原本不甘借助外力。无奈此间头绪繁多,下官已近殚思竭虑、心力交瘁,那日于州衙见了大人,确一时动了取巧之念。”略喘片刻,又道:“请大人代下官说明钱士清一案,或有方才大人所言意图;更紧要者,却是下官恐怕自己支持不到那末尾一场,便先省下气力,烦劳大人忙了一遭。至于旧屋内下官所言……”赵平勉强撑坐起来,道:“句句皆发自肺腑,绝无欺诳大人之意。当时下官已然觉察大人起了疑心,并不奢望逃过大人法眼,惟独希望日昳不被下官连累。”
荆非背转身去,许久方道:“为何定要杀人?”
赵平躺倒,又咳出些血沫:“若论杀心,怕是万卷楼火起当夜便有了。只因钱张二人毁了先生毕生心血。如今回想,这理由倒有为己推脱之嫌。大人说得不错:读书人禀性难移,唯恐惹祸上身,情急便下了狠心灭口。”
荆非回身,道:“以在下推断,赵兄曾于前三日去过张家,且并非一次。只是近日正逢节庆,镇上多有异地来客,故而张笈街坊不曾留意。”
赵平微笑。
“赵兄必是寻至张家恐吓张笈,先以与在下对钱士清之类似手法令张笈信服所犯之事已尽在官家掌握,继而伪称那伪本《春秋经传集解》必于曝书之日瞒不过众多藏书名家,钱士清见东窗事发,难免将一概罪责皆推与张笈,由此劝张笈不如将《春秋经传集解》真本交与赵兄,由赵兄暗中调换。张笈心计有限,听闻赵兄振振有辞,当下便怕了,于是约了时间交接《春秋经传集解》真本。张笈偷回刻坊仓库取出真本,又恐钱士清自碧沚园返回发觉事态有异,便发狠于刻版堆上做了手脚。以常理推论,凶犯犯事后必生逃逸之心。刻坊事发,赵兄却似颇有把握那张笈仍在家中。由此来看,张笈留在家中,仍出自赵兄一手安排。设法令张笈留在家中,却不为便于缉拿,而为方便赵兄灭口。”
见赵平咳喘连连、字不成句,荆非叹口气接道:“张笈已被赵兄唬住,必对赵兄言听计从。赵兄想是曾故作好心告诫张笈:务必留于家中,切忌盲动潜逃,以免官府反而起疑。张笈信了这劝告,虽自作主张于刻坊动了手脚,害下人命,但因自信官府必以意外了结此事、又兼以赵兄曾有劝告,益发稳留家中,如此即便官府来捕,仍不致落个畏罪逃窜口实。若官府依照常规,明派人马前去张家,张笈必被缉拿回衙,此举却于赵兄计划大为不利。只因赵兄所定灭口之计,只可于张家实行。”
“故而赵兄以保护《春秋经传集解》真本为借口,利用贺知州对自己言听计从之便,只安排衙役前往张家暗中监视。随后又以诳得《春秋经传集解》真本为由,说服在下扮作古籍商人前往张家。在下先前也曾疑惑,即便那张笈信服赵兄所言,然行凶毕竟重罪,以张笈疑心,他如何真能稳坐家中?今晨在下方明白这其中奥妙:一切只因张笈必须留下等人,等一与他利益相关之人。”
“想是张笈曾与赵兄诉苦,言称此次之事即便逃了官府,他家老爷亦必疑心于他,钱府恐是难以长留。以赵兄对人心之洞察,张笈此言怕是早在意料之中,于是赵兄顺势提出为张笈介绍新东家,这东家……惭愧——便是在下所扮京城书商。”
“毕老汉身亡至碧沚园曝书日不过三日。张笈返回仓库盗书为碧沚园曝书前一日,想必那《春秋经传集解》真本交接便于此日夜晚,而赵兄设法说服张笈交书怕是于早前一晚。在下到明州州衙正是曝书前一日,赵兄知晓在下身份,且知在下次日亦将前往碧沚园,便将原先所定之计依照在下心理重新打造一番,其中最大改动便是于当夜与张笈会面时提出‘京城书商’之事。”
“虽赵兄未必知晓张笈将于刻版堆内下手,但已料到钱士清事败后将被押回仓库取书。倘若《春秋经传集解》真本不见,钱士清势必归罪张笈,我等必对张笈有所动作,兼以赵兄坚持切勿打草惊蛇,暗访张笈之责难免落于在下身上。赵兄亦深谙这欺诳之法,所谓虚实相间,若皆为空造,极易败露马脚。在下需扮作书商方能引起张笈兴趣,而在下于书坊之事并不熟悉,此已为虚;若在下再硬将这一口京腔改了旁的方言,只怕更要弄巧成拙。正因如此,赵兄于曝书前一日便有把握告知那张笈:明日有位需雇伙计的京城书商来访;曝书当日,又与在下定下这书商暗访之计,在下也果如赵兄预料,自动进了‘京城书商’圈套。”
“赵兄听凭在下独自探访张笈,着实胆大心细之举。若换了旁人前去,只怕几句话过后便泄露出赵兄安排踪迹,偏是在下这自以为精明之辈前去万无一失。”荆非自嘲一笑,继续道:“进张家前蒙赵兄多次提醒:此计成败全在言语分寸把握。在下本就喜好玩弄词句,受了赵兄暗示、面对张笈时未免又刻意含混几分;而张笈一面,在下听惯了绕圈吞吐之话,只当张笈试探,全没想到在下与张笈谈得并非一事。直至最后,张笈始觉话题有茬,又见在下暗书‘春’字,终于悟到在下前来乃是买书,心下虽是疑惑在下何处得的消息,但见在下定金给得大方,便打定主意:先收下定金,避过昨日风头再寻赵兄问个究竟。如今回想这番攀谈,着实可笑,又或者理应感叹可悲,只因在下与张笈谈些何物并不重要,关键只在设法令在下前去张家与张笈喝茶攀谈——赵兄能否借在下之力将张笈灭口,关键尽在这壶茶上。”
“今日在下自一友人处听闻:张笈时常于州衙内吹嘘自家稀罕之物。钱士清曾赏张笈苦丁茶,怕也是赵兄于衙内顺耳听到。张笈为人吝啬但精于逢迎,平素不肯以好茶待客,只于贵客至时才取出珍藏之茶。张笈并不常住祖屋,将珍贵苦丁茶置于荒废屋内,初闻似有不通,但依张笈街坊所言,张笈每回祖屋暂住,必有异地客人来访。由此判断,那祖屋当是张笈代钱士清暗地买卖书籍所在,屋内所存苦丁茶,亦是为这班客商所备。日前赵兄前往张家,唬住张笈,张笈慌忙换了好茶招待。赵兄见是苦丁茶,证实此前所闻,待改日再次前往张家取书之时,便借口赏鉴茶叶,趁张笈不备,偷将有毒茶叶调换进罐内。”
“茶壶内所余碎渣乃是生附子。生附子多用于回阳救逆,赵兄久患心疾,心脉已衰,恐怕平日常用此药,若要多备一些,想来也并非难事。”荆非看眼陈未时,却见陈未时依然不动声色,只一手护住赵平腕脉。
“在下以剩余茶叶实验,发觉罐中只部分茶叶有毒。赵兄将生附子卷裹于茶叶之中、再经晾晒处理,外表与普通茶叶无异;若待茶叶润展,生附子却自然显现,浸泡水中。生附子浸液毒性虽不及直接服用生附子剧烈,但若多饮,仍可致命。”荆非一笑,“见这生附子浮现,在下亦不免一惊,想来昨日倒是拣了条命。因那张笈毙命时所喝之茶与在下先前所喝乃出自同一茶叶,若非在下福薄消受不起那苦兮兮的宝贝东西,待生附子充分浸溶,或许在下昨日也已一命归西。”
赵平凄然笑道:“下官怎敢儿戏大人性命?下官敢用此法,只因当日于州衙会面已看出大人并非嗜茶之人。”
荆非道:“倘在下推测不错,此计本是赵兄欲亲身施行。若赵兄亲身施行,仍可借用‘客商’一说将张笈稳在家中,贺知州那边只说是赵兄愿亲往张家试探便可。因赵兄平日多用附子所制汤剂,偶再饮些,并无大碍;不似那本有阳热之张笈,略多饮些便送了性命。”
赵平略一阖眼。
“生附子一事,在下也曾有两处疑团迟迟未解。一者,生附子需浸泡足够时间方可生效,赵兄何以确定张笈当晚必定继续品饮同壶苦丁茶?二者,赵兄虽可利用‘京城书商’之说诱使张笈取出苦丁茶招待,但昨日洗壶、选茶、注水皆张笈独自所为,且罐内有毒茶叶与无毒茶叶混杂,赵兄如何确定张笈定于昨日单拣出那有毒茶叶冲泡?今日在下终于明白,关键尽在‘吝啬’两字。”
“苦丁茶于江浙一带颇为昂贵,只逢有贵客来访张笈方拿出招待,平日张笈自己所喝不过些普通碎茶。昨夜在下拜访时间不长,苦丁茶却已泡上一壶,张笈舍不得倒弃,便续水又喝了半夜,直至生附子毒素累积发作,暴毙身亡。而令张笈自行拣出那有毒茶叶,若利用张笈心理亦不难办到。那苦丁茶茶叶有长有短,赵兄只需将生附子卷裹于明显细短茶叶之中、混入茶罐,以张笈吝啬本性,必将首选短小茶叶。”
“张笈平素便少与街坊来往,此时又避风头,自赵兄偷换毒茶至在下扮做书商拜访这一日内,必无其他贵客,如此张笈便当着在下之面,为自己泡下致命一壶茶。罐中所剩其他带毒茶叶并不只限于细短茶叶,恐怕一是赵兄为了保险,再也便于事发后嫁祸钱士清。众所周知,苦丁茶乃钱士清所赏。倘若碧沚园事发,张笈因茶中毒身亡,常人必推测乃是钱士清意图灭口;而若将生附子一味卷裹于细短茶叶中,一来易于暴露赵兄手法,二来不似钱士清心计所及。赵兄此计,称得上一石二鸟。”
赵平只道:“大人果真名不虚传。”
荆非摇头:“可惜最关键处在下终不明白。”
赵平笑:“动机?”
“不错。若为偷窃,赵兄已窃去《尚书》,却又将书留于碧沚园;若不为偷窃,钱士清既已伏法,《春秋经传集解》真本原可顺理成章归还原主,赵兄却为得《春秋经传集解》不惜杀人。在下不解。”
赵平眼中忽有异光闪过,示意陈未时将自己扶起,倚坐枕边,道:“大人可知万卷楼藏书将转与范钦?”
“今日范钦已去碧沚园搬书。”
“那地方志可被范钦取走?”
“在下特意问过去蚤,不曾。”
赵平欣然一笑:“如此下官便心安了。”回望陈未时,眼中一抹留恋之意:“日昳与下官父母早亡,蒙先生不弃,自幼跟随先生读书。若无先生慷慨大敞万卷楼之门,我等贫寒之辈如何得见那许多经籍。”
陈未时无语,转身离开。
赵平瞥眼陈未时背影,再看荆非,道:“先生门生众多,常有不良之辈偷窃先生藏书,先生亦不在意,常告诫我等书籍贵在流传,不在柜藏。可惜万卷楼却因此衰败。如今万卷楼藏书尽归范钦。下官早有耳闻,范钦嗜书如命,于所藏之书看管甚严。待范钦书楼成形,只怕先生日后若想见自家藏书亦难上加难。《尚书》为先生家传,虽不常道与外人,但下官知晓那是先生心爱之物。昔日我等可尽览万卷楼藏书,唯独这《尚书》被先生看管甚严。”阖眼略歇片刻,又道:“下官不才,枉费先生教诲,至今只做得个小小知事,怕是赔上下官毕生积蓄也无法保住先生所有藏书。下官自知天命不久,只想最终为先生留下几册心爱之书。万卷楼火起,下官知那范钦恐怕万卷楼藏书再遭劫难,必加紧购书,故当时便起了窃书之念。至于《春秋经传集解》,下官素知钱士清早年常自楼中窃书,可惜并无凭证,此次只算是新帐旧债一并算了。”
荆非道:“故而赵兄自书房窃去《尚书》,却并不带走,反设法令尧卿相信此书已经被窃,不再起收购之意;而那《春秋经传集解》,赵兄亦知:若直接归还碧沚园,仍将被尧卿购去,因而不惜以人命换下此书。”
赵平颔首。
“赵兄何以断定那地方志不会被丰老先生出售?”
赵平笑:“因为毕老汉。先生本是恋旧之人。”
荆非只觉疲惫不堪,仰首长叹,许久方道:“碧沚园一案,到此为止也罢。”
赵平微微摇头:“大人可还记得与下官许诺?”挣扎着自枕下摸出册书来,道:“万卷楼藏书既已出售,此书亦当物归原主。”
荆非接过那书,正是《春秋经传集解》。
荆非苦笑:“赵兄与在下约定将此案查明,原来是唯恐没有还书之人。”
“有劳大人。”
荆非摸出酒壶,慢慢喝下一口,望定赵平,终道:“你我之间,又何必说这许多官话?”
赵平目光黯淡,道:“下官岂敢。下官与大人早已分处律例两侧。纵有千般理由,下官终是犯了律例:且不论张笈之死,钱士清遭张笈毒手下官亦有罪责。”目光益黯,喃喃道:“可惜,等不及看大人升堂审案了。”忽又挣扎起身,紧攥荆非衣襟,促道:“那书……”
荆非只能点头。
赵平释然一笑,松了手劲,颓然倒下,目光散逸,渐没了气息。
二十
见赵平身子愈冷,荆非自身亦不由随着冰冷下去,尤以赵平曾紧攥衣襟处,益发冷得彻骨,连手中之书都险些抖落地上。
陈未时不知何时现身荆非身边,顺过荆非手中之书,略瞥一眼,复交还荆非,淡淡一句:“去者已矣。”
荆非眼看陈未时静静为赵平阖上双目,心中虽有疑问却问不出口。
陈未时反是看出荆非心事,回身依然淡淡道:“双九未曾与在下提及此间种种。但若此番没有大人,在下虽是不才,却也愿助双九了结心事。”
见陈未时眼中血丝绽现,荆非不忍多言,拿稳那书,沉一口气,缓步出门。
门外不远,贺知州守候一旁,荆非本欲掉头而去,但见贺知州无端亦现了老态,不由心下凄凉,上前长施一礼,无语而去。
又是碧沚园。
范府家丁果然手下麻利,不过两个时辰工夫,内院已尽空了。
荆非撇开去蚤,径直去那碧沚亭。
月湖景色依旧,略有风声,却不闻竹响。
丰坊独坐亭中,待荆非走至近旁,方缓缓回过头来,见荆非将手中之书郑重放下,亦只冷笑一声。
荆非平住气息,道:“此书乃先生门生赵平叮嘱在下交还。”
丰坊不语。
“另有《尚书》一册,合于昨日贺知州所赠地方志书页衬纸之内。”
丰坊嗤笑一声,仍是不语。
荆非识相,只道:“在下告退。”
丰坊眼望远湖,迸出一字:“坐。”
荆非坐。
丰坊回首,摩挲那《春秋经传集解》,一拍石桌,喝道:“不成器的学生!”
荆非道:“赵平殚思竭虑,只为将真本留存先生身边,此番心意,还望先生体察。”
“他若有心,为何不亲自还来?”
荆非只得道:“赵平已病故。”
丰坊闻言手下愈紧,木然片刻,低吟道:“何处人事少……”
荆非再度告退。
丰坊凸眼逼视荆非:“大人可是仍要追究赵平之罪?”
荆非无言以对。
“倘若赵平所窃之书并非真品,大人可否留赵平死后清静?”
荆非忽觉如坠冰窟。
丰坊叹道:“果真是不成器的学生。枉在老夫门下多年,真书伪书却分辨不清。”
丰坊起身,背对荆非,面湖负手而立,道:“事已至此,老夫也不瞒大人:所谓祖上自高丽访得《尚书》,不过是老夫看不惯当今那班文人乱释经籍,赌气伪造的古本。至于《春秋经传集解》,亦是老夫自蜀中找人做的伪本。为这两册无用伪书搭进自家性命,糊涂!糊涂!”
荆非不记得自己如何离开的碧沚园,只依稀记得离开时丰坊口中仍不绝骂着“糊涂”,声音却逐渐颤不成调。
当荆非终于看清眼前景物,发觉自己已无意间回到谢三小屋。
杯碗仍摆在桌上,屋里其他家常器物却已搬空。
谢三走了。
桌上留下张纸,是谢三的字迹。
“徒劳问归路,峰叠绕家乡。”
荆非自嘲一笑,挥袖推翻桌案,晃出门去。
(完)
(本文纯属依据部分史实虚构。)
[注释]
1)丰坊(1492-1563?)字人叔,一字存礼,后更名道生,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明鄞县(今宁波)人。丰氏原为鄞县大姓,历代为官,代出闻人。丰坊本人博学工文,尤精书法,家有万卷楼。黄宗羲《丰南禺别传》曾对丰坊有如下描写:“读书注目而视,瞳子尝堕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丰坊性情怪僻,不善治家理财,晚年家财丧失殆尽,其万卷楼藏书为门生窃去十之有六,后又不幸遭遇大火,所存佳本已无多。丰坊原与天一阁范钦交往颇深,早时范钦曾从万卷楼抄书,丰坊亦曾为范钦作《藏书记》,故万卷楼劫余之书尽售与天一阁,祖宅碧沚园亦转在范钦名下。
丰坊才学过人,但也因伪造古书在藏书史上留下颇多恶名。其中《河图》石经本、《鲁诗》石经本、《大学》石经本,丰坊谬称是其祖先清敏公北宋间得之于秘府;又有朝鲜《尚书》、日本《尚书》,谎说是其曾祖丰庆得之于驿馆。吴焯《绣谷亭薰习录》评说:“其著述未免欺人,其翰墨洵可传世也。”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则讥为“贻笑儒林,欺罔后学”。丰坊晚年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客死僧舍。
2)谢三故事,可参见《黄藤酒》。
2005-2-1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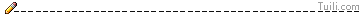
|
|
Ruhest du auch.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