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学华(郑学华) 郑学华(郑学华)
|
|
|
1 楼:
浮鹰岛往事(二)
|
02年11月11日23点00分 |
2、
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使我惊喜地跳起来。这声音虽然极细小、渺远,却坚定、明晰。我飞快地跑到海岬上,眺望远方。
夕阳红彤彤地悬浮在海天之间,施展着它无穷的魅力,把遼远的海天都染成金黄灿烂的一片。一艘帆船满载着金黄从金黄的深处缓缓归来。
父亲的船是当时整个海岛公社里最大的,船中央装着一桅很大的帆,张开来,可以包下大半艘船,船首还装着一个小些的帆。顺风之时,大帆小帆一齐张开,船便快速辟浪前进了。帆之于船是最普通平常不过的东西。奠定父亲的船在整个公社的地位的,是它还装了机器,25匹的马达!机器驱动的船整个乡里仅有这么一艘。机器保证了船在无风或风向不对的情况下也能快速直线地前进。不过为了省油,父亲的船仍然扬帆前进,很少驱动马达。只是在有重要事情需要赶时间时,才扬起风帆启动马达。
今儿一大早,村支书林之坪就来找父亲,要父亲赶到吕峡港接县城来的公安,返程时拐到西洋岛,接来乡派出所的干警。他们将要调查张有财的死因,给个说法。
父亲没说什么,立即就出发了。
傍晚,隆隆的机器声告诉人们,父亲的船回来了。
林之坪带着几个民兵站在砾石滩上迎候着。船直接驶上砾石滩,一个穿着便服的干部模样的人领着四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出现在船头上。船和无水的砾滩之间还有二三米浅浅的海水。林之坪认得干部模样的人是乡里的政法干部老方,便大声地叫民兵挽起裤脚,把老方和公安背上来。船上一个年纪大些的公安看了看同,立即脱下了解放鞋,挽起裤脚,卟嗵一声,林船上跳入水中,哗哗地涉上岸去。老方和另外的三个人也纷纷学着样儿,跳入水中,涉上岸。
上得岸来,老方介绍公安的给大家。年纪大些第一个上得岸的是县公安局刑侦科的何副科长;何副科长约略四十出头的样子,老方介绍他,他同大家一一握手。何副科长旁边胖胖的提着一个黑色大箱子的公安,是胡法医;胡法医冷漠地同众人点点头,算是招呼。另外两个是乡派出所的,林之坪都认识,一个是派出所所长赵飞虎,一个是干事刘晓。赵飞虎三十岁,长得敦实厚壮,这人深沉而富有心计,他曾经在浮鹰岛插过队,大家都认识他。刘晓是个一米八的大块头,二十三四年纪,十分不清秀可人。
林之坪同众人一一握手,口中不停地说着“欢迎欢迎”,然后领着大家向前去。
林之坪把大家领到自己家里,何副科长说:“大队部在哪里?去大队部吧。”
林之坪连忙说:“你看你看,大家都还赤着脚,先进来洗洗脚,然后再到大队部去,我向县领导汇报。”
于是大家就进去。
林之坪家是幢二层的砖瓦房,十分宽大,可是二层只搭着几根椽子,未铺上木板,只是“空中楼阁”,据说林之坪搭着偌大的框架,是希望他的两个都送去参军的儿子能有出息,将来把楼阁建设完整。
进入林之坪家,林之坪的女儿林芝立即迎了出来。她端来了温水给大家洗脸,然后再洗脚。
林芝是岛上的民兵连长,她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和草绿色的军裤,扎着一条皮带,飒爽而妩媚。
林芝端着一盆温水给赵飞虎,赵飞虎怔住了,低低地叫道:“依芝……”
林芝板起脸,放下脸盆,默默地走开了。
洗漱完毕,何副科长说不要去大队部了听汇报,先去现场勘查,已经发生的情况可以边走边汇报。
众人来到靶场附近,看见一爿竹床上躺着一个小小的用白布包裹着的躯体,已经散发出浓浓的怪味来了,一群苍蝇在四周飞舞。周围有几个人漠然地值守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看见穿着公安的人上来,立即冲了过来。
“还我的孩子啊!还我的孩子!”
妇人还未冲出两步,就被周围的男男女女抓住了。这妇人是死者的母亲黄菊花,一个寡妇。在此值守的大多是她家的亲属,也有风个民兵,奉林之坪的命令在那儿看着,以防什么意外。
何副科长面无表情地看了看妇人,示意胡法医验尸,自己则在现场仔细勘查起来。
胡法医放下工具箱,从中拿出口罩、塑胶手套戴上,伏在尸体上,仔细地查验着。
何副科长在埋尸现场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过来同胡法医一起验看尸体。一会儿,胡法医说:“尸体已经发僵,尸温不足20℃,以此推断,死者大约死于十七八个小时以前……也就是昨晚上10点半至11点半之间……窒息死亡,应该是窒息死亡。你看,在这,眼结膜下有出血点,不过面部和额部却没有明显的出血点,颈部也没有明显的青紫斑,气管和食道有一些泥土,但很少……我想必须解剖才能确定死因。”
“那你就解剖吧。”何副科长面无表情在说。
胡法医有些犹豫。“是不是带回县里解剖?”
“这不可能。群众不会理解的,再说,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案子上,你就在这儿解剖吧,确定一下死因就行了。”
“好吧。”胡法医无奈地从工具箱中掏出一块铁盆子,又掏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刀和剪,堆放在铁盆上。然后套上塑胶手套,小心地做完准备,举起明晃晃的手术刀,从下巴顺着脖子直切下去。
突然传来黄菊花撕心裂肺的哭叫,不知哪来的力气,她猛地从几个男子的手中挣脱,不顾一切地向胡法医冲来。还未近前,却被林之坪拦腰抱住了,几个民兵也慌忙上前拦住。赵飞虎见状,上前一步,猛一推搡,妇人倒在了地上。几个民兵一涌而上,把她的手脚一动不动地摁在地上。
“你们让他留个全尸吧,行行好,公安老爷,让他留个全尸吧,留个全尸……”黄菊花嘶哑地哭叫。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嗵地一声,跪在了地上。
“张家这一脉只这一个孩子,现在绝代了!你们就让他安宁吧,给他留个全尸!”
老人是张家的伯伯,一边说,一边泪流满面。
那一天我才真正明白,在我的乡人的意念中,死者是神圣的!一个人生之时就算是穷凶极恶恶贯满盈,一旦他死去,他的罪孽就消弥了。冤死屈死者也一样,都应该尽快地入土为安。
林之坪立即站出来向老人反复解释,说尸体解剖是科学,是为了了解死因,解剖之后还要缝合的,不是要肢解它。同时,民兵们立即站成一排,把两个公安保护在人墙中。
何副科长不为所动,他威严地站起来,大声地说:“我们这是在进行现场勘查和解剖,请你们不要阻挠我们,否则,你们就是破坏和攻击革命行动……”
林之坪吓住了,也不管老人怎么挣扎,叫上几个民兵,架起他,就送回村里去。
何副科长漠然地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
许久,胡法医阴沉着脸,极不情愿地完成了现场解剖。他用酒精洗手。
赵飞虎热切地说:“胡法医,你解剖的结果怎么样?”
胡法医阴郁地说:“颈部肌肉呈环状出血症状,集中在左右两侧,但舌骨大角、甲状软骨没有骨折;气管内有少量的沙土……这表明死者死前被人掐过,但没有致命,尔后被埋入土中……不过少量的沙土也有可能是死后被掩埋时掉入的。另外胃内的容物只能回县里做,我已经采样了……”
“采样不采样都一样,死者是被掐死的。”何副科长又问:“死者还有其它的伤痕吗?”
“没有了。”胡法医似乎缺乏足够的自信,语调也显得发软。“致死的原因应该是扼死,但凶手的力量似乎并不大……这样的伤痕并不足以致命……”
何副科长不满地瞟了胡法医一眼,陷入沉思。
旁边,赵飞虎却急急地插话进来。
“不,这些伤痕足以说明死因即是扼死。”赵飞虎坚定地说,“死者是个年仅11岁的儿童,儿童的喉部有弹性,窒息性暴力致死留下的痕迹很轻微,而且很快就会消失……这是儿童同成人在同一情节下的最大的区别。凶手在扼杀死者之后,--至少凶手是认为死者当时已经死亡--立即就将死者埋入土中。而当时死者并没有死亡,他还有微弱的呼吸--气若游丝。”
胡法医的脸更极阴沉了。他傲慢地问道:“你是说死者被埋入土中时还有呼吸?”
“是的,是这样。”
“那么如何解释死者的呼吸道仅有少量的土?”
“那是因为死者的口鼻都已被大块的泥土封住了--我询问过最初发现死者的几个人,他们都说死者被挖出来时,口鼻及耳朵都被人用泥土封住了。”
“是的,我也听说了。”那个英俊的干事刘晓在一旁说,“所长,你说的有道理,你的技术还真厉害。”
赵飞虎见自己的意见占上风,禁不住得意地转向何副科长:“何科长,你说呢?”
何副科长语中带刺地说:“看来你对这案子已经十分明了了,那还用得着我们来勘查?依我看,法医验尸,凭的是技术,暂时还用不着假想和推理,当然应该以法医勘验的结果为准。同志,你还年轻,还要多多学习啊。”
何副科长说完便不理睬赵飞虎。他对已经回到现场的林之坪说:“今天晚上开个全体党员和贫农骨干分子大会,我们要发动群众,查找线索,争取尽快破案。”
林之坪连忙说:“是是,我这就通知。”
何副科长背着手,走了几步,停下,丢下一句话来:“现场勘查就这样了吧。”然后径自走开了。
3、
村委办公室里乌烟瘴气。一盏汽灯挂在低矮的楼房中央,由于气打得不足,病蔫蔫地咝咝叫着,发出黯淡的光;这光线在各种劣质纸烟和各色水烟枪发出的充满了辣味的瘴气的包围中,更加黯淡了。
何副科长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这一端,脸色阴沉,一根接一根在抽着“水仙”。“水仙”牌香烟是当时我们县上能抽到的最好的香烟了。坐在办公室里开会的,多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农,他们一来就肆无忌惮地拿出水烟筒,抽起那种辣味很浓烈的板烟,尔后一边互相报怨着什么,一边脱下内衣,细细地翻找着虱子,找到一只,便捉到嘴里,很响地咬碎,却含在口中,也不吐掉,继续捉着虱子……只见喉节一阵蠕动,满口的血虱子竟然呑了下去!何副科长仿佛听到了骨碌碌的吞咽声,恶心得要呕吐起来。
在烦燥中,何副科长大声地叫了一声:
“开会!”
众人有些莫名地望着他,议论的声音小了些。
林之坪立即站起来道:“大家静下来,开会了。先请我们县公安局的何科长讲话。”
何副科长低声问林之坪:“ 人都到齐了吗?”
“差不多了,能来的基本来了。”
旁边,赵飞虎插进来道:“一堆的老头。你有没有通知村民小组长来开会?”
林之坪看了看低头捉虱的人群,说:“有几个没有来。”
“你有几个村民小组?来了几个村民小组长?”
“七个,来了三个。”
“这样的会村民小组长能不参加吗?你这个支书太官僚了。”
赵飞虎似乎有些吹毛求疵,有意找碴的样子。林之坪红了脸,直直地看着他,不说话。何副科长不满地瞟了一眼赵飞虎,大声地说:“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
何副科长先念了一段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语录,然后说这次浮鹰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请大家要提高警惕,积极提供线索,揪出凶手。特别是昨天晚上十点钟之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物在山上,或者有其它的线索……
人群中没有人嗞声。
何副科长又强调了几次,还是没有人嗞声。
这时候胡法医自以为是地说:“根据尸体解剖的情况,凶手可能是个力气较小的人,他先是掐了死者,见死者没有断气,就用泥土封住了他的口鼻和耳朵……”
何副科长是想到了这一点的,但他不愿意明说,希望有目击者能提供线索。胡法医这一说,打乱了他的计划,无奈,他也只好强调道:“胡法医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凶手可能是老人、妇女,也可能是个个头较大的男孩。对一个儿童下手,仇杀的可能性较大。同张家结过怨仇的人是我们重点调查的对象……”
“张家有什么?一个孤儿,一个寡母,现在孤儿已经死了,寡母受这打击,也有点神经失常了。”
说话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渔民,年纪大约四十七八。
林之坪向何副科长介绍道:“这位是孙长辉,二组组长,贫农,党员。”
何副科长见有人开腔,饶有兴致地问:“你知道张家有没有同谁结下什么怨仇?”
“死者的父亲原来跟我在同一艘渔船上的,他待人很好,天性乐观,从不跟人计较什么。六年前在避风途中不幸出了事故,掉入海中……他女人也守家,从没跟邻里红过脸。谁会跟这样的人家结下怨仇呢,而且怨仇这么大……”
这时胡法医又插话道:“有没有可能是儿童?儿童之间因为游戏的原因常常会结下怨恨……儿童的因素我们也不能忽略,一定要认真排查。”
何副科长也说:“是的,有关儿童的线索我们也要排查--昨天晚上是中秋节,小孩都参加了烧柴塔,他们有没有矛盾纠纷?这一点你们有什么发现也要说。”
“不,这完全不是小孩子干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无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赵飞虎站起来,环视了一下会场,郑重地说。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番话会令县上来的侦破专家下不了台。
“首先,我们先看看死者张有财在昨晚上最后的行踪。张有财那晚先在西区烧柴塔,后来西区为头的金贵叫他上山去捡柴草,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人看见他了。据我了解,那一晚的烧柴塔并不盛大,儿童们因为缺少柴草没有什么兴趣,烧了不久就散伙了,儿童之间也没有什么争抢、吵闹和打架。很多孩子都被打发上山捡柴草,但白天他们捡过了,知道没有什么柴草好捡,因此他们并没有上山,而是回家了,只有张有财真的上山去了,他没有回家。”
赵飞虎清了清嗓了,接着说:“其次,张有财的一只鞋子掉在山下,而他最终被埋在山里,我们可以肯定,他在山下同凶手进行了搏斗,可他为什么不大声呼救呢?他为什么不跑回家,反而住山里跑了?--这只有一个可能,他被凶手捉住了!凶手不但捉住他还掩住了他的嘴!张有财挣扎着,没有挣脱。而那只鞋子可能就是在挣扎中掉下的。”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凶手为什么要用泥土封住了张有财的口鼻和耳朵呢?”赵飞虎停顿了一下,白了一眼何副科长和胡法医,继续说:“原因很简单,那是一个仪式,一个杀人的仪式!而儿童根本是不会搞什么仪式的。”
胡法医看了看何副科长的脸色,十分阴沉,忍不住站起来说道:“我想请赵所长注意,根据验尸的结果,死者颈部的掐痕并不明显,这固然可能是因为儿童的颈部有弹性,但并不排除凶手力量小这种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搯死张有财呢?”
赵飞虎淡然一笑:“很简单,因为凶手以为张有财已经死了。”
“既然凶手以为张有财死了,又为什么还要用泥土封住他的口鼻呢?”
“所以我认为用泥土封口鼻这个行为是个在凶手看来有特定意义的仪式。”
胡法医红了脸坐了下来,却不服气地说:“这并没有排除凶手是力量弱小的儿童这种可能性--而且案件可能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复杂。”
“是的,案件可能并不复杂,但是破案却并不那么简单。”
“赵彪!”何副科长突然喝道,“你很了不起嘛!那还需要我们干什么,这案件就由你来侦破了。”
赵彪是赵飞虎的原名,自从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以后,他就改了名,不再用那不吉利的名字。
赵飞虎仍是有些调皮地笑笑,说:“我们一定要破了这个案子,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好吧,今天晚上的会就到这里,散会!”何副科长气冲冲地说宣布。
四个不欢而散的人又一起回到了林之坪家。家里,林芝刚开始准备点心,没想到会这么快就结束了,林芝和她妈妈一边煮点心,一边端来了温水,请四位领导洗漱。林芝给胡法医端来温水时惊惧地盯着他的手,仿佛看着这双手持刀割开了鲜血淋漓的尸体。胡法医不解地问:“我的手很脏吗?”
“不不不!”林芝红了脸。
给林之坪和林芝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住宿。何副科长就在林家睡,林之坪两个儿子参军了,刚好空着两张床;赵飞虎和刘晓则住到碉堡去,那里床铺多,宽敞,也比较舒适。
点心是一锅切得很大块的水煮鲳鱼。热腾腾的鲳鱼端上桌,大家都吃得满头流汗。何副科长和胡法医从未吃过如此甜美的鱼,不禁大声叫好,也不管赵飞虎在一旁阴冷轻蔑地看,放开了肚皮吃。何副科长吃饱了,也不看赵飞虎和刘晓,径直唤过林之坪,说:“县上有更紧急的案子,我们明天早上一早就走。”说完就睡下了。
只有赵飞虎在一旁冷笑着。
林之坪立即找到了我父亲,布置送县公安回城里。父亲没说什么,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开船送何副科长和胡法医走了。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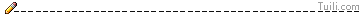
|
花非花 雾非雾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