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青(青青) 青青(青青)
|
|
|
1 楼:
北京司法改革又出新举措 刑侦人员首次...
|
02年05月06日01点24分 |
北京司法改革又出新举措 刑侦人员首次出庭作证
2002年5月5日 08:36 新华社
“证人朱继峰,你应当如实回答问题。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故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
“我听清了。”回答完这句话后,在法警的指引下,朱继峰在《人民法院证人作证保证书》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幕发生在4月17日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法庭当时在审理一起交通肇事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身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支队的交通警察,朱继峰和该支队事故科长王万荣分别以案件的侦查人员身份出庭作证。有专家称:“让刑事案件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在新中国还是头一次。”
事情还得从2001年12月9日的一起车祸说起。
当日,山东省单县农民韩宇华无证驾驶一辆小货车途经北京市丰台大桥西侧路口时,将行人王淑贞撞倒逃逸。因抢救不及时,王于当晚在医院身亡。丰台交通支队在对此案进行侦查的过程中找到并扣押了肇事车辆,但一直没有抓获韩。今年1月29日中午,韩宇华来到丰台交通支队,当韩向办案人员出示伪造的身份证和驾驶证,想以他人的名义领走肇事车辆时,被民警当场识破并扣留。直到晚上,韩宇华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肇事过程和买卖假证件的事实。
据出庭支持本案公诉的检察员、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处副处长陈阳介绍,案件起诉到丰台法院后,辩护律师曾想进行无罪辩护。辩护人提出了两个主要理由:一是公诉人如何证明死者就是韩宇华交通肇事的受害人;二是韩宇华并没有在丰台交通支队使用假证件。
针对上述问题,丰台检察院进行了严密的证据安排。一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在法庭上通过电子屏幕出示所有重要证据,二是通知丰台交通支队承办此案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4月17日,丰台区法院如期开庭审理本案。案件吸引了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厅室的负责人和数位知名法学家在内的上百人到庭旁听。在庭审的质证过程中,检察员陈阳一会儿通过投影仪展示物证,一会儿走下法庭,向被告人或证人发问,并面向法官总结质证情况和结论。当控辩双方就死者是否就是韩宇华开车撞伤的人进行质证时,警察王万荣和朱继峰先后出现在法庭上。两位警察就案件的发现和侦破过程详细作证。严密的逻辑、排他性的表述,连旁听者都清楚地知道了韩就是作案者。
谈到韩使用假证的过程,朱继峰和王万荣用事实说话,证明了韩出示假证、企图蒙骗警察以及后来承认的详细经过。“毫无疑问,你当天使用了假的驾驶证和身份证!”两位侦查人员的证词,让所有庭内人员确信无疑,就连被告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使用假证的事实。
一位旁听者向记者表示:“第一次看到警察以侦查人员身份出庭作证。这样的审判让我心服口服。”
本案的审判长张勇告诉记者:侦查人员的出庭,不仅使得案件证据更加充分,事实更加清楚,合议庭组成人员对此一目了然。也有利于旁听人员详细了解案件情况,让审判更有说服力。
在回忆出庭作证的经过时,王万荣科长深有感触。他向记者谈了作证时的一个细节:当王就公诉人关于警察前往案发现场的经过作了详细的陈述后,辩方律师又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本来觉得重复回答是多余的,但我想到,既然出庭作证,回答有关提问是义务,如果我只回答公诉人的问题而拒绝回答辩护律师的问题,显然会让别人误会我有偏袒之嫌。最后我还是认真回答了辩护律师的问题”。
王科长告诉记者,那天作证后回到单位和同事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出庭作证有利于促进办案质量,今后如果有机会,还是愿意出庭作证。
丰台交通支队副支队长孙振宝当了31年交通警察。他告诉记者,让警察出庭作证,这是多少年以来没有过的事了。这种做法有助于就涉及专业领域的事项向法庭和旁听人员说清楚。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侦查人员自身素质,让侦查人员在下次办案时更加扎实、更加注重依法办案。
陈阳副处长对记者说,在以往的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证据方面的疑问,甚至是证据不扎实的情形,一些细节问题不可能在案卷中有完全的记录。面对辩护律师的质问和反驳,公诉人往往被迫“补漏”。陈阳举例说,庭审往往会遇到被告人当庭翻供的情形,他们翻供的理由是“刑讯逼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检察员通常会以“只要有其他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就行”之类的话来搪塞。如果侦查人员作证,检察院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了。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蓝向东和汪长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基于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丰台检察院正在实行司法改革,包括立体质证、改变公诉人位置、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各项举措。蓝向东说,传统庭审中,控方往往只宣读证言,这不利于质证。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可以给辩方同等的质证机会,增强了交叉质证的效果,既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旁听人员对程序正当地进行认识。汪长青表示,丰台检察院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促进庭审方式的改革。
4月30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光权博士通过记者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充分的肯定。他说:“在英美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在我国,证人出庭率非常低。让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符合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辞原理,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对抗和平衡,对于发现案件真实,保护被告人权益有重大作用。警察出庭作证,为我国司法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对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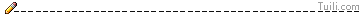
|
|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法律案例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法律案例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