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fst(苏菲斯特) sfst(苏菲斯特)
|
|
|
1 楼:
转贴(法律思想网):信息公开与政府公...
|
03年01月09日20点59分 |
信息公开与政府公信力
作者:萧瀚
——对中国诉陈正平(914投毒)案的初步研究[1]
官可使由之
亦可使知之
引言
2002年9月14日,在中国,在大陆,南京汤山镇发生了一起特大投毒事件。根据官方后来的报道,汤山镇作厂中学和东湖丽岛工地部分学生和民工因食用了油条、烧饼、麻团等食物后发生中毒,中毒人数300多人,死亡42人,经化验食物中含有违禁鼠药毒鼠强,警方初步认定此案系人为投毒案后,立刻展开侦破工作。9月15日凌晨5时,犯罪嫌疑人陈正平被抓获,9月17日,陈正平交代了作案经过,9月30日上午8:30,南京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检方起诉陈正平犯有投放危险物质罪,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陈正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陈正平提出上诉,江苏省高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院授权,核准对陈正平的死刑判决。2002年10月14日,陈正平在南京被执行死刑[2]。
此案即震惊中外的“914”特大食物投毒案,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将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诉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案,简称中国诉陈正平[3]。如此性质恶劣影响巨大的大案从案发到审结并执行,总共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其司法过程之神速高效实在罕见,这似乎是好事,似乎是超光速的正义而不是木腿正义(即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但是,作为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我又对这样的神速高效有所疑虑:象这样的大案为什么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量如此之少?从陈正平被抓获到处死的整个过程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所有行政行为、司法行为都合乎法律的规范吗?如果陈正平的家属或者如我等“多管闲事”者有疑问,官方提供了什么渠道可以解答这些疑问?如果没有这样的渠道,如果疑问无法解除,或者更加极端的说法——陈正平被冤枉了,怎么办?政府行为公开与司法独立以及司法正义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需要不需要设置具体可操作的行政行为、司法公开制度?人民苦苦希求行政公开、司法公开,而官方很不情愿,难道行政公开、司法公开仅仅是有利于人民而对政府毫无益处,甚至是坏处吗?
诸如此类,可谓百感交集,可是无论多少“感”,最后只集中到一感:政府要杀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它想。正是因为这一“感”,我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理论上说,在一个政府行为不公开的国度里,任何人都可能被秘密逮捕、秘密审判、秘密关押乃至秘密处决,因此学界已经有无数人在呐喊:行政行为应该公开,司法应该公开;以司法公开促使司法独立。诸如此论,闻声百里。本文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一个典型的新闻管制事件,以分析具体案件的方式探讨政府行为公开化的操作性规范,因为理念再漂亮美好,倘若“只能远观不能亵玩”,那也未免太奢侈了。
关于中国诉陈正平案——我们知道多少?
根据目前各类媒体对中国诉陈正平案的报道,以及网站媒体信息量开放度大于报纸杂志媒体的现状、并且集中了各种纸媒信息的特点,还有新浪网在大陆门户网同行中的权威地位,本文所依据的本案新闻资料主要以其为据。那么根据新浪网上的专题《南京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中的新闻资料,目前本案被关注的时间段为2002年9月14日13:59发布的第一条新闻《南京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 已有多人死亡》到2002年10月16日19:23发布的最后一条新闻《抓获南京投毒案案犯陈正平的乘警荣立一等功》,共历时33天,在这33天里,从案发到被告人陈正平最后被执行死刑,各大媒体发表的与食物中毒及毒鼠强相关的公开报道共95篇,其中直接与“914”大案相关的报道占53篇,公开发表在纸媒体的评论文章四篇,涉及的媒体遍及全国各地。上述数量的报道必定不是涉及此案的全部报道,但是根据中国媒体管制的现状,即使有未被收集在内的其他媒体报道,在内容上与上述报道差距甚大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要了解中国大陆媒体对“914”特大食物投毒案的报道情况,上述95篇新闻稿大致已经足够(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还搜集使用了其他国内网站上与此案相关的部分文章)。
那么从上述95篇新闻稿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什么情况呢,其信息量是否足够让人们对此案作出公允和最大真实可能的判断呢?下文着重讨论人们需要知道,但是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的内容。
一、陈正平被捕获前的报道(2002年9月17日 11:25之前)
从案件发生到陈正平被捕获前,媒体关于“914”大案的报道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发生开始的时间:2002年9月14日早晨,没有具体的时间;
2、案件发生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没有更具体的地点;
3、人物:中毒人数200多人,死亡38人,没有更具体的人名、身份;
4、事件经过:2002年9月14日的报道中只有100字左右的内容,到9月15日才有稍微详细的报道。
在陈正平被捕获之前,媒体关于“914”大案的报道基本上集中在新华社通稿的口径下,因此报道中出现不少奇怪现象,例如,关于惨案发生的时间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报道:9月14日早晨,由于各地作息时间的差异,对于早晨这一时间概念的理解,各地是不同的,而人们只能从中学生吃早餐中毒上推断,此事件大约发生在6:00-7:00之间或者稍晚一些;关于惨案发生的地点,9月14日的报道就很宽泛:汤山镇,这是一个很大范围的地点概念,而“肇事”小店和盛园豆浆店则到14日晚上9:13的报道中才出现,而绝大部分的报道则根本没有提及和盛园的店名,有些报道甚至拍了和盛园被查封的照片,却没有注明和盛园的名字;至于报道中出现的人物名字则更可笑,在此事件的报道中出现的第一个名字是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紧接着与他名字同时出现的是南京市长罗志军,报道内容当然不会是他们也中毒了,而是说他们亲赴现场,高度重视此事件,另有报道说:“(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省长季允石和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梁保华在外地接到有关报道后,立即作出重要指示。”[4]至于中毒者、死亡者的名字根本就没有集中报道过,直到9月15日的报道中,才出现第一个中毒者名字:汤山中学高一学生秦玉梅,而她名字的出现是因为记者想了解中毒情况,她的情况是中毒程度最轻的,而中毒死亡者的名字则一直没有见过,9月16日《健康报》刊发的《与死神争夺生命》文中以“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打工的民工田山、吴明盟”的中毒情况为开头,可是他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也没有交待[5]。也许报道中零星提及的中毒者名字还有一些,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见过死亡者的名字,只有38(1个月后是42)这个数字,在此事件中,中毒者的生命完全变成了数字,连不幸死去的人也不例外!
二、从陈正平被捕获到审判之前(2002年9月17日19:24 -2002年9月29日21:37)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各大媒体比较详细地报道了陈正平被抓获的过程,报道称陈正平对于投毒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报道其作案动机是嫉妒好朋友、同行陈宗武生意兴隆,所以投放毒鼠强。报道中出现的人物主要有抓获陈正平的上海开往洛阳的1659次列车乘警长崔万鸿、列车长郭喜梅,还有记者采访过的陈正平的生意邻居许夕云(《南方周末》),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厅长裴锡章、副厅长黄明立即率领刑侦局局长徐珠宝、政委吴大有赶赴现场,全力组织案件侦查。一个由省、市公安机关领导组成的专案指挥部迅速成立。”(《人民公安报》)[6]但是这一期间的媒体都没有对犯罪嫌疑人陈正平的作案经过作细节报道,也没有报道检方对案件可能采取的司法行为,甚至陈正平是在什么时候由检察院批捕的都没有报道。但是,9月29日的报道透露消息说9月30日将开庭审理。
三、从公审陈正平至今(2002年9月30日9:16至今)
报道称9月30日上午8:30陈正平被带到南京市中级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公开审理,到11:07中国新闻网就报道说陈正平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也就是说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审理之后一个人就被判处死刑。同日13:34人民网报道记者从庭审过程了解到中毒人数为300多人(依然没有准确数字),死亡人数42人,陈正平从农贸市场上花了8元钱购买毒鼠强,至于什么时间,哪个农贸市场,从谁那里买到,有没有目击证人,投毒过程的时间、地点、投放毒鼠强的剂量、有没有目击证人则一概没有报道。媒体也没有报道哪个检察院派员支持公诉以及主诉检察官的名字、有没有警察到庭作证、以及辩护律师的名字,而主审法官的名字或者合议庭名单一直就没有报道过,倒是二审审判长、江苏省高院副院长田幸在陈正平被执行死刑后的第二天接受央视采访。作为犯罪受害人的中毒者以及中毒死亡的家属有没有接到判决书以及其中有没有人不服一审判决而请求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辩护律师如何看待一审判决、对于案件的事实部分如何看待,二审程序如何运作的,各位法官的意见是否完全一致或是并不完全相同等等,也都没有任何报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到目前为止,连中毒的准确人数都没有调查清楚——也就是说到底有多少受害人没有查实——的大案却已经尘埃落定,被告人就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关于中国诉陈正平:政府还有义务要告诉我们什么?
本案在司法程序上已经结束,因此只要不涉及独特的办案手段(刑讯逼供除外),公布其中的主要内容及办案细节应当是政府的义务,作为民众,我们有权知道下列媒体没有或者无法告诉我们的内容:
1、陈正平购买毒鼠强的准确时间、准确地点、目击证人;
2、出售毒鼠强的人名字、身份,毒鼠强的来源;
3、陈正平投放毒鼠强的准确时间、地点(有媒体登出关于作案现场的照片,但却没有具体说明),以及投放的食品原料--是水还是面粉还是豆浆?投放毒鼠强的具体剂量?有没有剩余未投的毒鼠强以及毒鼠强外包装或者容器的下落。
4、陈正平投放毒鼠强时有没有目击证人;
5、中毒人数的准确数字,名单,身份证号;如果没有身份证,也需表明身份;
6、中毒死亡者的名单,身份证号;如果没有身份证,也需表明身份;
7、警方是如何确定中毒者包括死亡者中毒及中毒致死的原因系陈正平投毒所致;
8、警方办案人员的名单,身份;
9、警方向检察院提交案件之前的办案过程;
10、陈正平交待作案经过的详细资料;
11、警方有没有告知陈正平可以聘请律师介入询问,如果有律师参与,律师在警方办案过程中有何意见;
12、检察院审查警方提交的案件报告过程,检察官的名单,身份;
13、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理由,起诉书;
14、主诉检察官的名字,身份;
15、一审法院接到案件后审查的经过;
16、一审法院确定案件开庭审理前所作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在9月26日前向社会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17、整个庭审的过程,其中包括合议庭成员的名单、身份,主诉检察官的名字、身份,律师的名字、身份,证人的名单、身份,双方辩论的经过,质证的经过等等;
18、一审判决书;
19、陈正平上诉的时间、地点、上诉状内容;
20、生还的受害人以及死者家属有没有接到一审判决书,如果接到有没有表示意见以及有没有请求检察院提出抗诉;
21、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名单、身份;
22、二审法院审理案件的经过;
23、二审裁定书;
24、核准死刑的经过及其裁定书;
25、执行死刑的准确时间、地点;
上述内容作为构成一个案件的基本要素是公民们有权知道的——无论有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可否认,之所以报道的信息量少得可怜固然有媒体中人对法律尤其是法律程序不甚了了的原因,但是媒体管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无疑是主要原因。因此大量报道内容都受到严格限制,即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不公开。从上述25项(如果细分则会更多)我们应该能够公开获知而未能获知的内容上看,可以猜测完全是官方新闻管制所致,而不是媒体没有报道能力,例如到现在民众也无法看到此案的判决书,甚至连一审法官的名字都没有见到过,这就显得十分怪异,除了新闻管制,恐怕不会有别的原因——因为有一两个甚至一两百个记者缺乏报道能力是可信的,如果全中国的记者都弱智,那是不可能的。另外如死者的名单——如此重要的内容,既然官方已经承认死亡42个人,那么至少这42位罹难者应该是可以报道的,并且首先是官方媒体应当报道的,但是我们无法看到一丝一毫的报道,除了新闻管制,还能有什么原因?
虽然表面上看,我这样说只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猜测而已,但实际上有一些材料能够表明这样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有两篇材料可以部分地证明此猜测,一篇是来自sohu网站的文章,题为《南京市委宣传部就914特大投毒案的稿件(图)》[7],署名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 网络宣传管理处,基本内容就是局势如何被控制了,政府如何尽力救助中毒者之类,这些情况我相信也都是事实,只是与自由媒体(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的差别在于,后者的信息量会更大,内容也会更加丰富,该网页上还有南京市委宣传部原文的扫描件,根据中共宣传部的威力,sohu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都不太可能伪造这么一份文件,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看得出来它大致是真实可信的。另外一篇材料也是来自网络,题目是《9.14汤山投毒案的48小时[《南方周末》被撤稿]》,来自一塌糊涂站、锐思评论等多家论坛,该文的内容非常翔实,对于2002年9月14日在南京汤山发生的中毒事件做了详细报道,尤其对当时人们中毒的惨状做了细腻的报道,文末还附了24位死难者的名单,其中有名字、年龄和身份[8],这篇文章显然也不是伪造的,至于它是不是《南方周末》的被撤稿,我们没有100%的证据,但是以经验推断,我是相信的。
从这两篇材料来看,联系后来审判之后,依然信息闭塞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因为什么而导致了我们对于中国诉陈正平案会如此地无知——不是无知而是无法知。
行政、司法公开制度浅议:以本案为例
本案涉及的问题至少有四方面的内容:1、新闻自由;2、行政公开;3、司法公开;4、司法独立。限于问题的题域和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之间的关联,本部分只讨论行政公开和司法公开,尤其着重从部分法治国家现有的经验比较和本案所包含的关于政府行为信息中探讨它们的具体制度设计——由于限于本案,这样的实证研究只能是十分粗浅的。
一、行政公开
行政公开与司法公开一样是一个关于民主的问题,这在公诉案件中尤其体现得明显。在法治国家,政府行为应该向公众或者说是选民负责,如何负责?首先就是要被公众所知,公众只有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才能知道政府行为是否合乎法律的要求,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那么政府行为如何被公众所知就需要一套非常严密的程序来支持,按照这套程序,公众可以通过公共媒体获悉政府行为,而不会因为政府的强力被拒之门外,因此研究这套程序的设置就是一件头等大事--我们不可能光靠着呼吁公众有知情权就能够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
在一个政府行为方式暗箱传统深厚的国度,要设置一套政府行为公开化的法律程序无疑是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虚心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就可能会节约研究成本。例如,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由于国内学者从纯粹立法或者学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已有相当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重复这样的劳动,而是直接将本案融入到对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实证研究中,以突显制度设计的实践性。
以本案为例,从案发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终结,提交检察院建议提起公诉、递交起诉意见书之前为行政行为部分,即公安局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说,我们当然有理由要求行政部门公开此案侦察的全部经过,以检验本案在侦查过程中公安局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如果我们借鉴美国或者日本的现有立法,那么,我们不妨假定中国已有信息公开法,并假设这样一个虚拟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例:
张三是犯罪嫌疑人陈正平的好友,于2002年9月20日获悉“914”投毒案侦查阶段终结,因为关心此案,他向南京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公安局提供关于本案的侦查信息以及犯罪嫌疑人陈正平作案的详细资料。
我们不妨继续假设,中国的“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消息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因此,从原则上讲,南京市公安局有义务公开本案的侦查信息。张三的申请根据法定格式,即在专用的统一格式申请书上填写下列内容:
(1)张三作为申请人的姓名以及住址或居住地。如果张三以单位名义申请,则此项当填写为法人或团体的代表人的姓名;
(2)行政文件的名称,例如起诉意见书,或者不知道行政文书的名称,但是其他足以将公开请求的行政文件特定化的事项,例如“陈正平投毒案”或者“914”大案。
接着,张三应当将此申请书递交给南京市公安局长,并且按照规定缴纳申请费用,要求公开有关信息。南京市公安局长接到申请书之后,应该根据“信息公开法”的要求决定是否公开张三所申请公开的陈正平涉嫌投毒案的侦查信息。虽然,法律规定行政行为的信息原则上应当公开,但是法律也考虑到某些信息的公开可能会严重影响公众利益,因此赋予行政机关首长以自由裁量权根据具体但法定的情况决定是否公开,不公开或者部分公开。在本案中,南京市公安局长可以援引类似如下条款“行政机关的首长有相当的理由认为公开可能妨碍犯罪预防、镇压或侦查、支持公诉、刑罚执行及其他公共安全和秩序维持的信息。”[9]而在张三提出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不公开或者部分不公开决定。张三若对此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要求复议。对复议结果依然不服,则可以根据法律提起行政诉讼,若法院生效判决支持不公开决定,则申请信息公开的程序终结。
在虚拟本案中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南京市公安局长认为张三之申请公开的信息中有部分是可以公开的,例如中毒人数的清单以及死亡者的清单,则按照信息公开法决定公开,同时决定以复印件的方式公开,张三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公开决定实施手续费,同时被涉及的清单中的人或者死者的家属按照信息公开法成为本信息公开案的第三人,在信息公开前,局长有义务向他们告知张三的申请,第三人有权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公开还是不公开的意见书。局长接到意见书之后,可以决定公开还是不公开。如因此而在第三人中产生异议,则可能导致复议申请及其后的诉讼,程序终结后实施公开或者不公开。
由于中国诉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2002年9月30日公审,因此本虚拟信息公开案件的程序经过,在时间上可能与此事件之间产生某些关联,那么根据信息公开法的一般原则,本虚拟案将因此而发生变化,即南京市公安局长可能会随着公开开庭时间的到来而决定陈正平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的全部侦查信息公开。
根据一个如此简单的虚拟案例,我们无法窥见信息公开法的全貌,甚至只见到一点极其零碎的内容,但是从这个虚拟案例中,我们也许能够比较真实地感觉到信息公开对于行政行为民主化的重要意义。
在信息公开方面专门立法的国家,法律一般对于哪些内容应当被公开,哪些内容不能公开,哪些内容暂时不公开,哪些内容永久不公开(如果有的话),哪些内容在什么情况下公开,以及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哪些应该或者可以公开的信息中至少应当包含什么,行政首长有什么样的自由裁量权等情形都作出详细规定,同时当信息公开申请人对于被驳回的申请不服时,法律也规定了具体的补救措施,设置特定的机构或者通过司法来确定行政首长作出不公开信息决定的合法与否。美国同时还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必须公开举行会议,公众可以向政府获取相关的会议材料。在信息公开法领域,有两个问题往往特别不容易权衡,第一个是确定不公开信息的范围,美国的《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有九种情况下的信息不公开[10],日本的信息公开法规定了六种信息不公开的情形[11](关于两国法律该部分规定的比较,本人拟将另文详述,此处不赘),都对涉及外交秘密文件以及损害法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的内容做了不公开的原则性规定。倘若以中国诉陈正平案而论,即使在开庭审理之前,似乎也很难从法理上找到足够的依据将本案信息保守得如此严密,至少有些信息的公开并不会妨碍本案的公正审理,例如,中毒人数、中毒死亡者名单等等,但是我们看到,本案信息中除了陈正平的名字、抓捕陈正平的几名乘警的名字等极少量无足轻重的信息外,其他信息被行政部门全部屏蔽掉了。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大陆有些城市的行政部门已经开始朝着开放型政府转型,他们将一些行政政策上网,便于人们查询,即所谓的“电子政府工程”,虽然这些地方政府仅仅公开他们的部分政策,大量应当为公众所知的信息还未能够公开,但是与旧有的“全息暗箱操作”相比,总归算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立法界、法学界已经酝酿制定《信息公开法》,也许在未来两年里,立法层次的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二、司法公开
如前文所述,中国诉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虽然于2002年9月30日在南京市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审理后,陈正平就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尔后,陈正平提起上诉,被二审法院迅速驳回,2002年10月14日上午,陈正平被执行死刑。这一整个过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任何细节性的报道,本文所列出的25项内容只是十分基本的信息,但我们至今无法知道,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基本的司法公开问题。
由于司法公开是一个原则性的规范,在中国诉陈正平案审判的当时,要了解本案,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援引[12],事实上,我们至今也没有可援引的包含具体程序的法律规定。尤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起案件有众多的庭审现场旁听者,可是却没有相关的细节报道——别说细节,就是“粗节”都没有!——本文所述所列政府至少应该向公众公布的25项内容,在媒体报端丝毫不见。倘若以美国或者日本《信息公开法》相比较,作为不公布的理由的所谓“公布这些信息可能妨碍司法公正”问题在经过了司法程序之后,该理由应当不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的详细材料应当向社会公布,但是南京市政府以及江苏省政府并没有公布上述25项内容,显然,审判前的信息不公布行为并非因为担心信息公开会扰乱司法过程,而是另有它因,但南京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都没有作出任何有关解释——也许对政府而言,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政府行为传统,根本无需解释!
而在新闻自由的国家,即使法律没有关于法庭审理如何向公众公开方面非常明确的规定,新闻媒体的利益本身就能够使得这些案件都得最大限度地报道,公众从这些报道中获得的信息根本不必依靠另外的法律程序去获得。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诸如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赋予法官充分的司法独立,法官在运用这项权力时充分考虑媒体无孔不入的能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决定是否公开审判,是否不允许记者进入采访报道——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就有法官为此吃官司。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法官不让记者旁听,记者也没有起诉法官,判决产生之后,媒体还是可以自由报道审判过程的。比较中国诉陈正平案件,媒体好像集体装聋作哑——这当然是假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不敢报道。并且,可以想象,司法部门也一定早被打了招呼,任何涉及审理的法官、检察官,其面对媒体的发言限度是明确的,那么是谁定的这一发言限度呢?——不用问,大家都知道。在此情况下,中国目前的政府模式下,司法不独立的现状中包含了司法行为的封闭性,尽管最高法院在大量的文件中声称要司法公开,要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充分透明,而且与以前相比,也做得越来越规范,但是在涉及一些大案要案的时候,他们的非独立身份就导致他们自身必然受制于更有实权的党政部门,即使他们希望能够公开报道的案件也因为缺乏独立性而难以做到公开。但是,这种不能公开的黑锅却必须由司法机关背着,暗箱操作的骂名也就由他们承受着。
就中国诉陈正平案本身的信息公开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政治化依然是今天中国不变的现实。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一开篇就探讨新闻自由问题,那么这起案件所涉及的问题根本不值得写这么一篇文章,因为太过于常识。但是,如果把视角稍稍转换一下,从政府行为尤其是行政行为的公开化角度入手,我们就会发现,倡导政府行为公开化本身将大大有利于新闻自由的实现,尤其是倡导行政行为公开化更能够显示它对突破新闻封锁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倡导政府行为公开化的另一面必然包含着新闻自由的理念,只是前者来自政府,而后者本应来自社会,社会被政府劫持,政府不履行行为透明义务,民众就丧失了知情权利。
三、公诉案件行政信息公开与司法信息公开的关系
就一般而论,公诉案件的政府行为,其信息公开的标准和程度、渠道都有一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案件本身获得公正处理和让公众知情权得到满足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均衡,因此这种不同标准设定的目的也是为了既能够满足公众知情权,又不妨碍案件的公正处理,于是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法律如何来平衡这样的关系?
在法律确定性规范作出平衡以后,可能还会留下一些法律无法特定化规范的信息公开问题,这时应当由谁以何种标准解决法律难以直接决定的信息公开问题?同时,案件即使已经公开审理并且宣判,是否所有与案件相关的信息都应当公开呢?例如,以本案而论,在陈正平被公安机关抓获以后到案卷移送到检察院之前,公安机关有没有公布本案信息的义务?
这涉及到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原则,由于犯罪嫌疑人在经过公开公正审理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被假定是无罪的,因此侦查阶段公安机关获得的信息从法律意义上讲都还不能算定论,这时如果公开侦查信息就会导致舆论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利倾向,从而也可能直接妨碍接下来的司法公正,因此各国法律一般不向公众公开在此状态下的警务信息,但是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律师以及家属应当有权获悉侦查情况,但是在某些严重暴力及性方面的刑事案件中,为了保护受害人或者其他相关人的隐私权,公安机关会将某些隐私信息过滤后向信息公开相对人公开,这些信息在司法过程结束以后同样也属于不公开信息;或者某些犯罪情节的细节如果公开会引起不良的诱导作用,也会被列入不予公开之列;或者某些案件中涉及第三人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不宜公开的秘密,也会被列入不公开信息。我们从前文所引的日本信息公开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到,侦查信息并非属于不公开信息,而是行政首长可以决定其不公开,换句话说,行政首长也可以决定其公开,关键在于行政首长如何判断,在此法律赋予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拥有自由裁量权。并且在对待辩护律师或者辩护人以及被告人及其家属时,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就与对待公众时不同。由于检察院的功能与行政部门相似——除了它的监督法院功能之外,因此其信息对外公开的标准和渠道也应当与公安机关类似。
由于司法公开是一项原则,因此到达司法阶段,开庭审理就会产生案件信息公开的客观效果,但是,这里依然涉及到司法部门自身信息公开的义务,这不是单靠着一句抽象的公众知情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法律必须同时规定司法部门的信息公开义务,因为没有可操作的具体制度支持的司法公开,依然只是一种抽象公开而不是具体公开,例如法院虽然公开开庭审理中国诉陈正平,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也被法庭旁听人员听到,但是,如果检察院或者法院不允许人们查阅起诉书,那么这种公开还是不完整的,其他的庭审材料,其是否可以被查阅则不可一概而论,但除了上述起诉书之外,不少其他重要材料是否可以查阅也大致能够说明类似情况。
讨论这个问题是完全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美国,一切经过开庭审判的案件,都在法院中存在一份向任何人公开的档案,所有人都可以去查阅,除了按照法律规定不得公开的私密性信息之外,其他的与案件相关的材料,法院不会藏起来,不让人查阅——这才是真正的司法公开!这是他们的司法传统,一种深入民众意识的惯习,因此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这方面具体的规范性文件来约束他们公开司法信息。而我们的司法公开只是写在法律上的四个字而已!最高法院2002年11月15日公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民事案件材料的规定》也没有规定民事案件终结以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否可以查阅案卷——更不必说与案件无关的其他人!因此,中国所谓的“司法公开”实际上是一个“虚词”,民事案件尚且如此,刑事案件则更是可想而知!鉴于此,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我们必须讨论有关司法信息公开的操作性规范。
因此,在司法公开领域应当有具体的规范,以确定人们可不可以公开查阅庭审材料?如果可以,在什么阶段可以查阅?查阅的范围是什么?查阅之后是否可以以复制形式或者摘录方式带走?不同类型的案件,其司法信息公开的标准和渠道是否有差别?如果申请公开人对于案件的司法信息公开中的具体问题有异议,法律将以何种方式解决争议?或者如果某些司法信息不可以查阅,那么理由是什么?发生争议如何解决?等等,同时这里的司法信息是一个普遍性概念,即不仅仅包含了公诉案件也包含民诉案件及其他所有类型案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有实证的研究基础,而后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规范,保证司法机关履行司法信息公开的义务,满足大众的知情权。
结语:政府如何获得人民信任?
先秦典籍《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饵谤》中就提出言论自由将使人民和国家财富同步增长,其真知洞见堪为叹止。西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也早已证明对新闻的恣意控制将降低社会的总福利,宪政制度的实践和理论也表明恣意控制新闻将导致对人类基本自由的侵犯,恣意控制新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对言论的事先限制。但是,今天的思想家们早已证明,人民仅仅拥有新闻自由、表达自由,还是无法有效地控制政府权力,如果政府可以将其行为过程完全保密而不对公众公布,那么“保密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排他性占有,来扩张自己的权力”(斯蒂格里茨,1999、1,《环球法律评论》2002秋季号,页263)因此,为了使得政府行为能够被人民信任,就有必要要求政府公开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信息公开能够打消人民的疑虑,杜绝不实谣言的散布,因此作为政府而言,只要出于公正之心,则不怕公开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政府的行为不喜欢向民众公开,未必就一定是心中有鬼不敢公开,而是另有它因。
例如,不少政府官员继承着中国文化中含蓄的传统,不肯将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过度地让外界所知,这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的职业素质中缺乏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加以区别的观念,也就是缺乏这样的基本宪政观念:在公共领域内的行为应当接受大众的监督。同时,中国历代官治民模式的政治思维还难以在大众之间根本性扭转,官本位意识使得政府习惯了被过度关注和娇宠,因此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就首先只考虑自己的便捷或者本部门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拒绝考虑他们所应服务的人民利益,这导致在许多情况下,愿不愿意公开信息成为官员施展自己权力、检验自己权力大小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什么坏事也没做,但就是不想告诉你们。”他们常常不必思考人民是否满意,因为中国民间社会力量还很微弱,不足以对政府的非法行为构成真正的制约。《汉书·刑法志》里说,春秋时,“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理由是“先王办事都是按照固有的原则办,而不预先颁布法律。现在你将法律公布了,老百姓都知道了,就会起争抢之心,这样就会不利于治理……”可见那时政府力量的巨大——随时可以生杀予夺,人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法律!而且这种思维方式随着时间的流淌,两千多年来成为了一种顽固的文化基因,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妨碍了人民的生活。政府虽然在短期内似乎工作便利,如鱼得水,可以轻松自如地对付人民,但是这种状况必然是短暂的,明智的政府不会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它会认为获得民心才是头等大事,而如实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人民,则必然获得信任,获得民心——因此西方就有人不仅仅视信息公开为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同时也视之为一个大众心理学问题。
中国诉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虽然早已尘埃落定,可是由于我们获得的信息量太少,以至一直就有许多猜测,比如有些人就认为陈正平未必是真罪犯,由于至今关于此案的档案材料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这个案件的许多疑问,人们也会继续猜测下去,这对于江苏省或南京市政府的司法公信力也好、行政公信力也好,都将产生消极影响。
也许这起案件只是中国每天发生的千千万万起案件和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表明,由于新闻管制和政府行为不公开,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都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要扭转这一局面,只有一条路:还新闻以自由,置政府于阳光之下。
2002/12/23初稿,2003/1/3修订
注释:
[1]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华东政法学院的朱芒教授、北大法学院行政法教研室的沈岿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师何海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谢鸿飞博士的帮助,初稿完成后北大法律信息网的编辑曹乃婷硕士也对本文提出了重要的具体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谢意。
[2] 详见新浪专题:《南京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http://news.sina.com.cn/z/nanjingzhongdu/index.shtml
[3]也许无论是没有法律知识背景的公民还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士对于这样的案件名称可能都会不很适应,按照惯例,在中国大陆的民事诉讼中,案件名称一般是使用“张三诉李四购销合同纠纷案”这类非常清晰表明原被告双方及案由的规范命名,唯独在刑事诉讼中,案件名称从来都是控方缺位的,上述案例必定被命名为“陈正平投放危险物质罪”,这样的命名方式当然并不是一种错误的表述,但是它绝对不是完整和严谨的法律表述,同时在实际效果上容易造成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弱势地位被忽视,从心理学上看,当这样的案件名称进入人们大脑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必然是被告人,而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检察院则很轻易地就被思维屏蔽掉了,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很容易地被调整到只注意被告人犯罪嫌疑而遗忘检方办案程序是否违规,这样的案件命名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映了中国司法超职权主义模式的本质。为了纠正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本文认为应当对所有案件的命名均采用完整命名的方式,尤其是刑事案件的称谓必须突显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地位。
[4] http://news.sina.com.cn/c/2002-09-14/1756724604.html
[5] http://news.sina.com.cn/c/2002-09-16/1119727036.html
[6] http://news.sina.com.cn/c/2002-09-20/1143734742.html
[7] http://news.beelink.com.cn/20020918/1208329.shtml此为beelink新闻网上的文本,该文本声明本文转自sohu网,但是我到sohu网搜索本文时,无法打开该专题及本文,该专题的域名为http://news2.sohu.com/28/85/subject203178528.shtml
[8] 详见http://www.1488.com.cn/bbs/showAnnounce.asp?id=343691&boardid=27&Page=2
[9] 引号里的内容来自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教授朱芒先生翻译的日本《信息公开法》,该文本电子版由朱先生提供,在此谨致谢意。类似规定也出现在美国的《信息自由法》。
[10] 参见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下册,页1117-1118,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11] 参见朱芒《开放型政府法律理念和实践——日本信息公开制度》(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环球法律评论》2002/冬季号,页466-476。
[12] 虽然1979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试行)》第八条规定:“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新闻记者采访。记者凭人民法院发出的采访证进入法庭,可以记录、录音、录相、摄影和转播。”但是,这不能算是司法公开,因为记者在这里是没有自由采访权的,而是必须由法院发给采访证,法院不发,记者就不得采访。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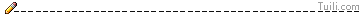
|
|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法律案例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侦探推理 > 法律案例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