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chzhch(行列式) zhchzhch(行列式)
|
|
|
1 楼:
晴雪记
|
04年01月17日11点28分 |
本帖是精华帖,目前处于免费状态,点此开始收费
晴雪记
霁后斜阳,天光青紫,寒意初生。
一人闲立帘前,半面微哂,修长的食指在窗台的积雪上划字, 疏松的雪与光滑的手,却印下如锥画沙的力度和质感。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张石。苍蓝的眼镜泛着离合的光。
老友卫源一直坐在炉前注视,这时忽然开口:“我知道你是高度近视,戴上眼镜仍是近视,对于一个以观察为专业的评论家来说这可真是奇闻。”
“是么,这副眼镜做工精良,度数还不很低,我只为老友才戴,表示对你的‘重视’。能得到这般礼遇者亦仅区区一二子。我在你的立场上深感荣幸。说真的,这世界万物,其价不过秋毫耳,又皆琐细如秋毫,那又何必明察?但是我知道你这‘评论家’三字弦外有音,这个职业所需的冷静、缜密、渊博实在不亚于你这‘艺术家’呢。”
“好个冷静、缜密、渊博,足下俱备,在下亦然。但我,艺术家,还多了一腔热血!我复仇,我出谜,我以热血起草我的谜语,我以热血描绘我的插图,我以热血书写我的答案,我以热血签下我的姓名!啊,为什么要和你讨论血呢?我会被你的血冻伤的。热血,我有;头脑,我俩都有;评论家,我的朋友,你又比我多了什么呢?”
张石用钢琴般清冽的低音说:“眼睛。”
“明辨的眼睛,观察家的眼睛……高度近视的眼睛?……那么让我见识一下,分析点评一下窗外那个骑车人吧,她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
“你会明白评论家的眼睛与众不同。但是请小声,我高度近视的秘密只有两三人知道。不过我有点怀疑,你确定这画面真值得一看么?”
“哦,这女郎真像大理石,朴质,细腻,又有文彩,又有内涵。她值得用你最好的水晶眼镜来看。”
“呵呵,我试试,你我的眼光大抵一致。不过为什么是水晶?水晶有双影……看到了。你的评论?”
卫源缓缓说:“我也当一回评论家:素色长大衣,非常典雅。她胸口有重叠的别针痕迹,曾经佩过胸花和校徽。这意味着天性高贵,家庭富有,正在求学阶段。她左手通红,看来那只手套已经遗失两三天了。于是索性只给不灵便的右手戴手套——她是个左撇子。”
“否否。雪地骑车需要怎样的小心谨慎啊,惯用手若冻僵有多危险。这女郎显然是右撇子。”张石做了个手势,“你想,这样一双小手好几天都冻着,她必然离开父母独自住着;而她不立即买新手套,说明她在本地还有家庭。就像我们早上出门忘了手表之类,只需等待回家一样。”
“那么正如刚才我所言,本地居住求学者,必非等闲。一个矜持又娇贵的女郎,却早早自立,又不是自己要脱离家庭。她的父母何在?还活着吗?那个家庭又有谁?关系如何?呵,这人简直是天生的女主角,柔软的双肩负着几宗血海深仇!”
张石抚掌:“足下三句话不离本行。”
卫源沉浸其中:“是的。复仇,复仇,我的本行。我对同道有天然的感知。尤其是这个大理石般的女郎,有一种无法掩饰的气质,我愿意为她复仇!谈谈白璧微瑕,她外套最后一个纽扣系着,这样骑车很不方便,下车时容易绊到。一个上等女子怎能这样粗心大意。看来她是十万火急来找你。”
“否否,她原来不是骑自行车的。长靴上的半尺雪痕说明她踏雪有一段时间,至少到雪停,也就是3:45。雪最深时反而突然骑车,的确是有急事。”
女郎疾步入室,躬身施礼。
张石款款开言:“姑娘失怙,漂泊不易。”
女郎答:“族人血洗殆尽,唯与家兄相依为命。”
张石惊立起:“令兄还健在否?”
女郎亦起:“正为此事前来。”她突然掏出一张黑色的名片,“我们处在谋杀的阴影下,已经很久了。”
卫源上前一步抓住女郎的手:“他可为你破案,我可为你复仇!”
三人沿着女郎来时的车辙来到一座五层小楼前。半尺深的足印小巧而清晰,犹如大白瓷盘的一圈缠枝花纹。环绕在中间的一个年轻人与那女郎一样容颜姣好,故而惊骇之色更觉狰狞。薄衣轻飏,素手僵直,手表搭扣已断,斜斜飞出数尺,有若残星,依稀闪光。方圆丈余即上文圆圈内白雪无瑕。圈外又有笔直的一道足印、一道车辙,延向相反的方向。
张石指着那直的足印说:“你什么时候到的现场?是徒步前来吗?”
女郎垂首:“大概4:00左右。因为我每周都是这时回家——就是家兄的公寓。”
卫源对张石说:“啊,老朋友,你说过她每周回家,又说过她刚才一直踏雪。”
张石点头:“没错。她雪停之后踏雪前来,来时路就是这直的足印;她绕尸体一周,就留下这圆圈;车辙是她去我们那里的印记。所有痕迹深浅一致,意味着雪停以后形成的。同理,尸体上并无均匀白雪覆盖,说明坠楼也是雪停以后发生的。雪停是3:45,死者坠楼时间是——”张石用手杖拨过来那块摔坏的手表,换了一副眼镜端详,“3:50。”
“坠楼?”
“呵,这一点聪明如你绝不会怀疑吧。死者既然没有留下足印,自然是从楼上飞下来的。呼……陨星化为碎片,从这微不足道的五层小楼?奇哉怪哉。你知道,大量研究和事实结果,24米以下的跳楼在国际上是不推荐的,尽管我不肯定从五层坠下不能死。他不是自杀,当然也非无意识地,身体完全放松地飘落,那样更无伤害,何况温柔的雪层为他的着陆铺上厚厚的棉花。这个年轻人呵,星落之前已然心死。他焦虑,他脆弱,他的神经极度紧张,他的筋骨也因此僵直,一个布娃娃从五楼落下可以毫发无伤,但他是个瓷娃娃,摔在地上碎成一千片。为什么要如此长篇大论呢?你们只消看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是惊恐杀害了他。姑娘,这一定与你家的世仇有关。”
“的确,”卫源凝视着她没有表情的脸,“你我一样是在世仇中长大的人。我们太熟悉杀戮与被杀,这是个可怕的习惯。别人的坚强是可爱的,我们的坚强是可怕的。他预知你的身份,你毫不惊异;亲人之死,你如此平静,几乎让我的朋友张石以为你并非不愿意这事发生。让我温暖你的手,过分的冷漠与你的年龄是不相称的。你……贵庚?”
“二十。”张石答道,“你在一年之内失去了父母手足。我们很难过。”
女郎瞪大双眼。
张石戴上一副金属眼镜,摩挲着那块亮晶晶的表:“多好的一块表啊,不是么?真正吸引我的,不是表盘上指示案件发生的时间3:50,也非表链上零星镶嵌的宝石,而是背面这复杂的图案。是你家的徽章吗?这并不重要,我不认识你们,何况这家庭只剩两人。哦,无论如何,是你们的父母定做的赠与的纪念品,我注意到中间的XX字样——二十,不是别的,当然是你们二十岁生日纪念,这对他们宠爱的孪生儿女。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庄严幸福的场面,然而不到一年,受赠者失去了赠与者,儿女失去了双亲。仅仅不到一年,因为这块表上还没有多少划痕。很抱歉因这块表触动了你的伤心事,正如案发时很可能也是这块表触动了令兄的神经。
既然说到时间,姑娘,你3:50以后到达现场,绕行尸体一周,骑车离开,前后不超过5分钟。你每周都这个时间来么?如果不下雪,是骑车来么?这辆女车是你的么?你的车不在你自己的住所却在令兄的公寓?就是说即使不下雪你也无法骑车前来?而命案发生却恰好有一辆车在此待命?数月无雪你都没有骑它?为什么车上没有锈迹没有尘土只有雪痕?这车闲置在这儿多久了?”
女郎昂首,从容应对:“诚如尊言。事实上,今天下午2:00我本骑车前来。途中微雪。上楼时家兄正在午睡,未敢打扰。小坐片刻。下楼。薄冰已凝。无法骑车,停车树下,徒步离开。4:00左右再来。”
张石深含赞许,不过镜片颜色甚浓,二人未察。
卫源叹道:“果然无瑕。姑娘既知令兄的午睡习惯,又早早前来,而后再来,是否有要紧事商量?”
张石用那张黑色的名片托着沉甸甸的手表:“就为此事!”
三人上楼。
张石目力不佳,只管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卫源一边走,一边对女郎低语。
死者的房间昏昏暗暗,不辨昼夜,全被低垂的长幕映成绛红。半墙皆书,也半床皆书。一几、一椅、一铁床,全是最简单、最舒适也最高档的,乱七八糟但一尘不染。淡淡的火腿味在空中浮动。有人称为混乱,也有人称为温馨。床头烟缸尚有余烬,旁边一个日记本压着一个精美的信封,这是很典型的年轻人的可爱的布置,除了信封里露出的半张黑色的名片。
晚风徐来,张石关上窗户,回头对卫源说:“你在给她讲那个羊皮帐簿的故事么?”
卫源浅笑:“我也想到了那个故事,然而一定不是你的答案。”
“否否。”
“那故事和这案子却也相同。”
“否否。”
张石已经摘掉眼镜,却仿佛有一层无形的眼镜相隔,别人什么也看不出,惟有刺目的寒意。这是命令的眼光么?也许不是,因为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别人做什么,但事实上它的力量又无法抗拒。
于是卫源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有个某人,他的仇家是个为富不仁者,所有赃证都在一本羊皮帐簿上。罪恶的主人杀掉了所有有意于帐簿的人,然后把帐簿藏得更加隐秘,每天起床时检查一遍。他的住宅是不易窥探的。这位‘某人’找了郊外一间无主的空房,精心布置成那坏人卧室的模样,又把那坏人麻醉后放进去,加以监视。‘某人’想,他醒来翻找的不就是藏帐簿的地方吗?我到他家对应的地方取不就行了吗?谁知道那坏人七翻八找找不到,大叫一声坠楼死了。……你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吗?”
女郎平静地说:“真的。”
卫源含笑:“这就是我和张石相识的案子呢。”
“而那死者就是我的叔父。”女郎注视卫源脸色变化,“我感激那个杀他的人,因为叔父亲手杀死我的父亲。”
“这样啊,这样啊……”卫源说,“侦探,也就是张石啦,他很惊讶于案子的简单,哦,有点幼稚,那时我们还年轻……”
“其实很容易知道那不是死者的家,他的老宅什么气味都可能有,却不该有廉价油漆味和掩盖油漆的香水味。” 张石清冷的声音,“而本案倒真是一个‘家’。这倒奇哉怪哉,因为密室大多在凶手熟悉如家的地方而非死者的家。”
“密室?”
“雪地是广义的密室。”张石竖起一个手指,“然而这是不必要的密室。浪漫型密室伪装灵异,现实型密室伪装自杀,这个案子既非前者……”
“不是自杀。”女郎应声说。
张石瞧着女郎点头。
“死者生前受到威胁已经多久了?这封索命的信是何时寄来的?死者的心理压力何时达到最大以至崩溃?姑娘,你俩常常会面讨论家仇的问题吧?一起吃饭的时候?瞧,他的书签就是上周六的帐单:鲫鱼汤一份,香烟一包,这是他的;酥焖羊肉一份,果汁一杯,这是你的,姑娘。你们商量预告信的事么?预告信大多没有涂毒,我们看一下如何?黑色名片一张,一日,括弧,周六,10:20,索命,哦,一日不是明天吗?今天命案就发生了!这年头的人没规矩极了,可是若连自己的预告都不遵守未免令人伤心。为什么是10:20,不是整点?似乎10:00别的地方要发生某事,你知道么?”
“给我的预告信上是10:00,我的宿舍到这儿20分钟车程。”女郎答。
“奇哉怪哉,预告10:20杀的人,死在了3:50。”张石对于数字细节过分兴奋,连周五周六的偌大差别都忘了,“写预告信的人摆明是谋杀,无须制造密室,这种人甚至狂妄得不给自己留不在场证明。而真凶的不在场证明——密室?否否,下雪是偶然事件,顺便说一句,表停止走动也是偶然。朋友,我们的阅历足够我们设身处地替凶手考虑一下时间问题,他必须不在场,他又必须赶到现场充分早,让尸体尽快被发现,确定死亡时间,来印证他的不在场证明。3:50案件发生,他并没来,他是2:00来的,地上泥水干涸程度说明他的确是2:00来了又去,然后4:00再来。请注意,凶手的计算中没有一个偶然事件!大家都是完美主义者。呵,我憎恶那些没有死者或是闲人帮忙就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不是凶手,而是骗子,作弊的赌徒不会幸运!……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言归正传,凶手要准确把握案发时间,就要为死者定时,是的,现场只有死者一人,凶手为他的每一个行为规定了时间。这就是手法。
啊哈,手法是案件的华彩部分,我们先来一小段铺垫。朋友,再给你一次机会回答左右手的问题:推断一下死者如何?”
卫源环视:“从家具摆设来看,死者是左撇子。”
“然。但我是从他捻烟蒂的方向看出来的。”张石展示帐单上香烟的灼痕,“这位姑娘又不吸烟,看看她的手指就知道。”
“等一等,你说定时,但房间里并没有钟。”
“一个散漫的年轻人没有钟并不希奇,何况这人有一块漂亮的表。问题是,当他看表时,当他睡眼朦胧地看表时,表上显示的是什么时间?一颗毫无防备的柔软的心得到了怎样的打击?不是别的,就是那个索命的10:20!”
“啊!”
“昏暗的小屋,年轻人凑近窗口看表,然后毫无知觉地倒向帘幕,从落地长窗飞出……”
“就像羊皮帐簿的故事。他也错了?他看错了?”
“否否,是你我看错了。表在地上,你我用右撇子的习惯看来——3:50;表在腕上,死者读数的方式却是……”张石把表拍在桌上,几乎嵌进去,猛地旋转180度,“这样!”
“10:20!”
“原来凶手2:00进来,替午睡的死者拨表……和打开窗户。”卫源深深吸气,“姑娘,你不再是天使了!”
张石双指夹起精致的手表,扬着头说:“如果我是凶手,我倒不愿拨表留下指纹。凶手根本不需要拨表,确切讲,不需要拨死者的表,我想想,呵,不需要拨任何一块表。凶手仅仅为他换上一块表,一块同样有钻石点缀,同样有旋转图案的家徽,同样有XX字样的,却是右撇子用的表!是的,那是作为死者的双胞胎拥有的一块表,是凶手自己的表。凶手很容易把自己的表擦得没有任何指纹,倒戴在死者的右腕;拿走了那块左撇子用的表,上面布满了死者的指纹。”
“同胞杀害同胞,死亡代替死亡。”张石逼近女郎,冰凉的镜片几乎贴上她雪白的额头,“一切都是对称,旋转的图案,双边的文字,错位的时间,谬误的生命。惟有谋杀的阴影看不出对称,因为只是一片浓黑。”
女郎甚至没有一丝颤动,刚强冷静如大理石。她默默取出一块同样贵重的,左撇子用的表,放在黑色的名片上。
“动——机?”卫源对张石说,又似自语?
张石静静地把一对表擦净,包好。
“请你务必给我一个动机,尽管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长项。”
张石转身。
卫源抓住张石的胸饰大吼:“我不能相信这位高贵的女郎会自斩手足。只有你喜爱没有动机的谋杀!只有你这,这……”
张石用冰凌般的双指拈他手腕,放下去,说了四字:“我们走吧。”
回到张家,卫源已完全嘶哑:“冷血的蛇哟,你为什么拒绝给我一个动机?”
“因为我一说,大家都会流泪。”
张石端端正正摆好两块表,轻轻地抚摩。
“你所谓‘自斩手足’,我称为‘壮士断腕’。从死者的日记可以看出,他恐惧,他无助,他受威胁,他受煎熬,他没有生趣,他不愿受辱。如果杀一人可以利……”
“啊,他应该自杀!”
“否否,他不能自杀,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他在周六不吃肉,只吃鱼。恪守规矩的人有福亦有苦。日记里还说那个仇家发誓不手刃他就自杀,所以他衷心希望早脱苦海。钟爱他的妹妹就让他死在最爱的人手里。试问天下还有更好的死法么?助人升天的人是值得祝福的,正如赫剌克勒斯赠给菲罗克忒忒斯神箭。而手足之情呵,又不相同。手足断,不可续,然而毒蛇噬手,壮士断腕。这种勇气只有爱之如己才能迸发。我也有一个灵犀相通的妹妹,所以此情刻骨铭心。你,朋友,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不知你能体会么?”
卫源重重点头:“我许多年来刻苦复仇,不就是为了亲人么?哪怕并无一面之缘。”
张石不语,只是把一对表贴在心脏位置。
“纪念品你是否和令妹分享?”卫源说,“对了,我记得你有给案件评分的习惯,满分十二,这个案件……?”
“十分。”张石把指针拨到十点,“有事凭它来找我。” 二人各得一块,“记住这个奇妙的雪夕。”
|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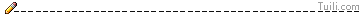
|
FROM MATH’S AID AND ART
NEVER WILL FAME DEPART!
|
※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
|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您当前的位置:
推理之门 > 原创推理 > 原创小说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06128号 推理之门 版权所有 2000-2024